也谈无效宣告程序中的“权利要求的进一步限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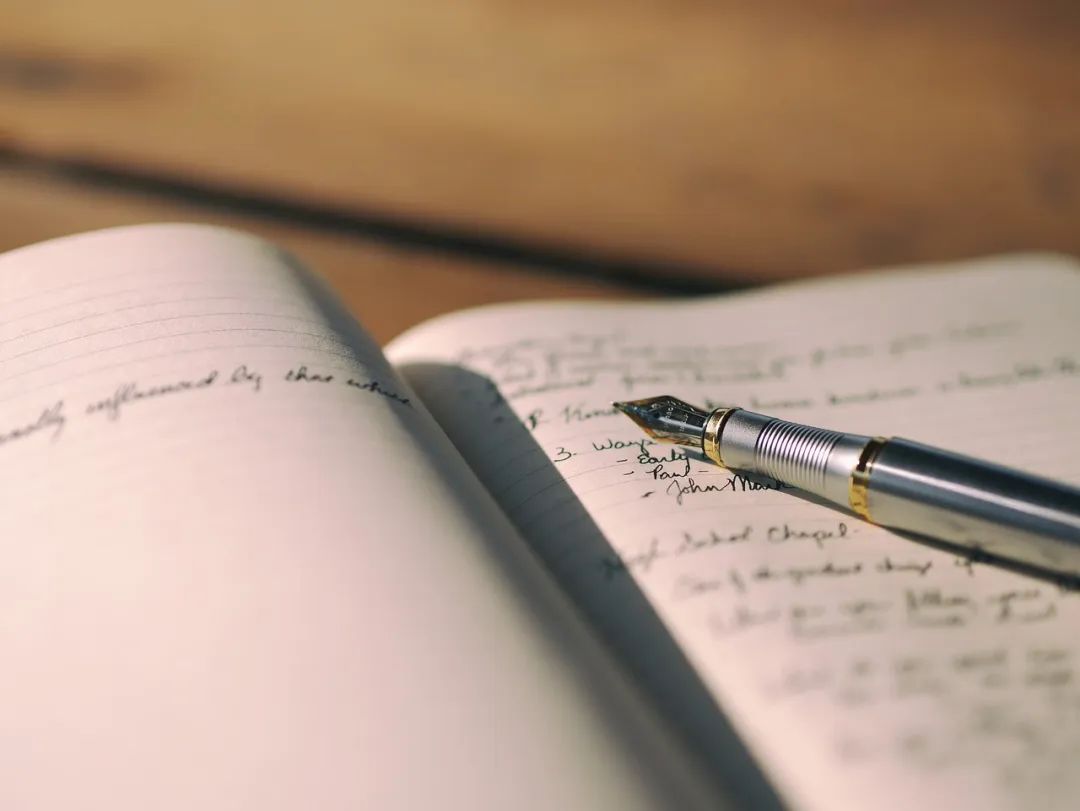
作者 | 黄辉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非全日制研究生
在2024年12月5日,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和无效审理部举行了第十一届创新主体交流活动。专利复审和无效审理部的审查员作了名为“专利无效宣告程序中权利要求修改的若干问题”的讲座(下文简称“无效修改讲座”)。本文就无效修改讲座指出的修改限制政策,提出笔者的观点和建议。
1
“权利要求的进一步限定”的修改限制政策
无效修改讲座中宣讲了专利无效宣告程序中“权利要求的进一步限定”的具体政策,引起了与会者的着重关注与讨论。尤其是主讲者宣讲的以下修改限制政策:
1.1 被修改的“原权利要求”在作出修改后,成为了一项新的“修改后的权利要求”,原权利要求在权利要求书中已经不再存在,不得再次成为被修改的基础。
1.2 修改之后“放弃修改”或“回退”至原权利要求,在审查指南中没有依据。
1.3 可以接受的修改方式是“一一对应的一换一”…… “一改多”( 即“同一权利要求”的进一步限定形成多个权利要求——笔者注),因为修改前只有一个权利要求,其实质上属于增加权利要求,也不符合“回应式修改”的原则(指专利权人应针对无效宣告理由或者合议组指出的缺陷进行修改——笔者注),是不能被接受的。
主讲者宣讲的上述修改限制政策,之所以引起了与会者的着重关注与讨论,笔者认为原因是与会者从《专利审查指南》(以下简称《审查指南》)找不到上述修改限制政策的原文依据,与会者从《审查指南》的现行规定也无法直接地毫无疑义地得出这些修改限制政策。
2
复审和无效审理部制定修改限制政策的依据
事实上,这不是复审和无效审理部第一次宣传这些修改限制政策。2017年4月1日起,修改后的《审查指南》开始实施,原《审查指南》第四部分第三章第4.6.2节中“权利要求的合并”调整为“权利要求的进一步限定”。2017年11月8日,当时的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即撰写了一篇文章名为《对“权利要求的进一步限定”的理解与适用》(以下简称《理解与适用》一文),发表于中国知识产权报/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网[1]。其主要内容也是宣传上述修改限制政策并从体系解释和目的解释两方面给出了政策的依据。
《理解与适用》一文的“体系解释”部分指出[1]:可以参考《审查指南》中实质审查程序与专利文件修改相关的规定,“举轻以明重”,来把握无效宣告程序中修改专利文件的尺度。《审查指南》第二部分第八章“实质审查程序”第5.2.1.3节“答复审查意见通知书时的修改方式”中规定:在答复审查意见通知书时,对申请文件进行修改的,应当针对通知书指出的缺陷进行修改,“主动增加新的独立权利要求,该独立权利要求限定的技术方案在原权利要求书中未出现过”,则属于没有针对通知书指出的缺陷进行修改的情形,是不予接受的修改方式。可见,在修改规则相对宽松的实质审查中,增加权利要求的修改方式通常都是不被接受的,其理由是修改应当针对审查意见作出,而增加权利要求的方式则通常不被认为是针对审查意见作出。授权程序与确权程序着眼于解决不同的问题,授权程序是对权利要求的布局进行构建,而确权程序中专利权人是对质疑作出应对,确权程序中允许的修改尺度应当严于授权程序,这是由二者的程序分工不同所决定的。在前程序中不允许的修改方式,在无效程序中也不应当允许。
《理解与适用》一文的“目的解释”部分指出[1]:“首先,增加权利要求,尤其是增加新的独立权利要求,通常会改变原有的权利要求书的层次体系。其次,无效程序的启动是请求人针对授权文本提出无效理由,以每一项权利要求或技术方案为请求无效的单元,专利权人应当针对无效理由作出修改。如果专利权人在一个权利要求的基础上,通过修改重新撰写出多个权利要求,将会超出请求人提出无效请求时的预期,使得请求人面对难以预计的程序负担。最后,授权权利要求的公示作用对于社会公众而言尤为重要。稳定的权利要求书以及有限的、可预期的修改方式,是社会公众明晰专利权利边界、准确评价自身经营活动法律效果的基础。”
无效修改讲座中主讲者口头提出一个观点,指出上述修改限制政策的法律依据是专利法规定“宣告无效的专利权视为自始即不存在”。主讲者认为无效程序中被修改的“原权利要求”等于被宣告无效,所以自始即不存在,所以无法再次成为被修改的基础,也无法“放弃修改”或“回退”至原权利要求,也无法成为“一改多”的修改基础(主讲者认为“一改多”等于多次修改)。
3
最高人民法院对修改限制政策的态度
无效修改讲座中指出的上述修改限制政策,部分已经明确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背书。在“(2021)最高法知行终556、581、738号”案件的裁判要旨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2]:以克服无效宣告理由所指缺陷为名,而行优化权利要求撰写之实的修改,即非回应性的修改,因其不符合专利确权程序的制度定位,可以不予接受。……对于非回应性修改,即便其未超出所谓“信息范围”(即“记载范围”——笔者注)和“保护范围”且属于专利审查指南所允许的修改方式,也可以不予接受。例如,权利要求的修改缺乏与修改相对应的无效宣告请求和理由的,一般可以不必再审查其修改范围和修改方式,径行不予接受。又如,在同一行政审查程序中,针对一项权利要求的无效宣告理由已通过对该权利要求的修改给予了回应,且修改后的权利要求已被接受时,对该原权利要求的另行修改及相应获得的更多新权利要求,因一般已不再具有回应对象,故可不予接受。
笔者顺带提醒读者的是,《理解与适用》一文中提出的修改限制政策也有未得到最高人民法院背书的部分。《理解与适用》一文中提出[1]:专利权人在未对原权利要求进行修改的情况下,仅通过对权利要求书中的特征进行组合增加了新的从属权利要求来进一步限定原权利要求。实质上,专利权人未对原独立权利要求或从属权利要求做出任何限定,因为原权利要求在修改行为之后仍还保留,没有体现“以缩小保护范围”的要求。这种修改方式不属于《审查指南》允许的“对权利要求进一步限定”,不能被接受。
最高人民法院在“(2021)最高法知行终548号”案判决书中指出[3]: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权利要求书中记载的无论是独立权利要求,还是从属权利要求,每一项权利要求均是一个完整的技术方案,拥有各自大小不同的保护范围。在2017年修订的《专利审查指南》中,并未规定专利权人采用进一步限定的修改方式时,必须对独立权利要求作出限定。在2017年修订的《专利审查指南》中,并未规定专利权人采用进一步限定的修改方式时,必须对独立权利要求作出限定。……国家知识产权局对于未修改独立权利要求,而仅修改从属权利要求的修改请求不予接受,没有法律依据……。
这次无效修改讲座中,虽然主讲者没有提到“(2021)最高法知行终548号”案,但宣讲的内容显示专利复审和无效审理部已经接受了该判决的精神。主讲者指出,无效宣告理由认为独立权利要求及其从属权利要求均存在缺陷,专利权人仅对从属权利要求作进一步限定的修改,这样的修改可以接受。从《理解与适用》一文中不接受,到无效修改讲座的可以接受,显示出专利复审和无效审理部当初制定的限制修改政策也并非言之凿凿的有法律依据。
4
笔者的意见
但笔者认为,“理解与适用”一文的“体系解释”“目的解释”及无效修改讲座主讲者口头提出的观点,均很难服众。修改限制政策的依据,值得商榷。
可以明确的是,从《审查指南》的字面规定得不出上述的修改限制政策,所以“理解与适用”一文、无效修改讲座均不从《审查指南》的文义上解释上述修改限制政策。
但“理解与适用”一文的“体系解释”,存在逻辑推理不周全的缺陷。因为审查意见答复中不能接受的修改之一“主动增加新的独立权利要求,该独立权利要求限定的技术方案在原权利要求书中未出现过”针对的是“主动增加新的独立权利要求”,不包括针对审查意见增加的新的独立权利要求。根据该规定进行逻辑推理,也只能推理出在无效宣告程序中,不能主动增加新的独立权利要求,而无法推出在针对无效宣告理由或者合议组指出的缺陷进行修改时,也不能根据“权利要求的进一步限定”的规定增加新的独立权利要求或从属权利要求,更不能推理出“一改多”不符合《审查指南》规定。此外,“理解与适用”一文认为“增加权利要求的方式则通常不被认为是针对审查意见作出”过于武断,与审查实践不符。
此外,“理解与适用”一文的“目的解释”,在说理上存在缺陷。笔者认为,“权利要求的进一步限定”这种修改方式,即使是修改出一项权利要求,也改变了原有的权利要求书的层次体系、并可能超出请求人提出无效请求时的预期(在技术特征繁多的情况下,请求人可能预期不到专利权人对权利要求的进一步限定具体会是怎样的限定)。“理解与适用”一文在这方面的说理,并无法说服大家,为什么修改出一项权利要求就符合《审查指南》规定,修改出两项以上权利要求就不符合《审查指南》规定。“理解与适用”一文也并没有阐述为什么修改出一项权利要求是有限的、可预期的修改方式,修改出两项、三项权利要求就不算是有限的、可预期的修改方式。如果非要认为“一一对应的一换一”修改符合立法目的,“一对二”等修改就不符合立法目的,可谓典型的五十步笑百步,无法服众。
为了阐明笔者的观点,笔者举个简单的例子,某专利权包括独权A+B,从权A+B+C+D,无效宣告程序中如果专利权人将独权A+B,修改为A+B+C(C来自于从权A+B+C+D),按照“理解与适用”一文这被认为是有限的、可预期的修改方式;如果专利权人将独权A+B,修改为A+B+D(C来自于从权A+B+C+D), 按照“理解与适用”一文这也被认为是有限的、可预期的修改方式;但专利权人修改出两个独权,分别为A+B+C、A+B+D,为什么就不是有限的、可预期的修改方式了呢?“理解与适用”一文也并没有进行周圆的阐述。
无效修改讲座口头提出的观点也无法逻辑自洽。被修改的权利要求,如果是完全等同于被宣告无效的权利要求,视为自始即不存在,不得再次成为被修改的基础,那么自始不存在的权利要求,自然也不能成为第一次修改的基础。而且按照无效修改讲座口头提出的观点的逻辑,修改的基础只能是自始存在的其他权利要求,那么“权利要求的进一步限定是指在权利要求中补入其他权利要求中记载的一个或者多个技术特征,以缩小保护范围 ”实质上变成了“从其他权利要求中删除记载的一个或者多个技术特征,以扩大保护范围”了,这明显是违背《专利法实施细则》的规定的,显示出无效修改讲座口头提出的观点理论逻辑不自洽。所以,笔者认为专利法规定“宣告无效的专利权视为自始即不存在”无法为上述修改限制政策提供法律依据。
综上所述,上述修改限制政策,虽然部分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背书,但法律依据仍旧值得商榷。笔者预计修改限制政策还会遭受专利权人的挑战。尤其是专利权人已经尝到了挑战《审查指南》及相应政策的“甜头”的情况下。
2017年修改《审查指南》,将“权利要求的合并”调整为“权利要求的进一步限定”,就是专利权人不断挑战《审查指南》的结果。《理解与适用》一文中部分修改限制政策最终被废弃,这也会鼓励专利权人一方继续挑战修改限制政策,即使是最高人民法院已经通过裁判背书——毕竟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也可以被新的裁判推翻。
因此,笔者预计将来还会有很多无效案件,专利权人与复审和无效审理部会在修改限制政策上争执不断,拖长无效过程,浪费社会资源。
值得注意的是,将“权利要求的合并”调整为“权利要求的进一步限定”,对应的法律依据是《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七十三条(2023年《专利法实施细则》),修改前的法律依据是2010年《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六十九条。实质上修改前后法律依据是一样的,因为所依据的条文内容没有变化。这说明国家知识产权局在落实专利法、专利法实施细则时,所采取的政策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与时俱进。当然,联想到以前国家知识产权局对修改前的《审查指南》相应规定的合理性及其法律依据的解释,给人一种改前改后都有理、都有法律依据的感觉——显得不是很严肃。
5
笔者的建议
笔者撰写此文,并不是不赞同确权程序对专利权人权利和社会公众信赖利益的平衡。笔者也不是鼓励专利权人去挑战修改限制政策。笔者撰写此文,期待的是立法的明确性。
立法的明确性,不仅是法理上的要求,也是立法法的要求。立法法规定“法律规范应当明确、具体,具有针对性和可执行性”。目前无效程序的上述修改限制政策,在《专利法》《专利法实施细则》《审查指南》均没有原文依据,而复审和无效审理部则不断宣传从体系解释、目的解释方面可以找到依据,但其说法却如本文评价的那样,不甚周圆。
笔者建议,不如将这些修改限制政策上升为《审查指南》甚至《专利法实施细则》的规定,以减少因为法律不明确带来种种问题,也免得复审和无效审理部费力宣讲相关政策。这些问题,不但包括浪费社会资源的诉累,也包括专利权人“踩坑”被伤害,比如被修改的“原权利要求”在作出修改后修改之后不得再次成为被修改的基础,又比如不允许“放弃修改”或“回退”至原权利要求,这些修改限制政策并没写在《审查指南》中,对专利权人而言真是深坑!
笔者建议最好是将无效宣告程序中的修改方式及修改限制政策,写进《专利法实施细则》。《立法法》规定:没有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依据,部门规章不得设定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范,不得增加本部门的权力或者减少本部门的法定职责。在《审查指南》中规定修改方式,在执行政策中规定修改限制政策,显然违背《立法法》上述规定。因此,笔者认为最好的做法就是将无效宣告程序中的修改方式及修改限制政策,写进《专利法实施细则》。
注释
[1] 刘铭,刘洋,对“权利要求的进一步限定”的理解与适用[EB/OL]。
http://www.nipso.cn/onews.asp?id=38583,最后访问日期:2024年12月20日。
[2]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专利确权程序中“进一步限定”式修改的审查;专利确权程序中权利要求修改的回应性要求[EB/OL]。https://ipc.court.gov.cn/zh-cn/news/view-3036.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4年12月20日。
[3]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2021)最高法知行终548号行政判决书[EB/OL]。https://enipc.court.gov.cn/zh-cn/news/view-3020.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4年12月20日。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知产力立场)
封面来源 | Pixabay 编辑 | 有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