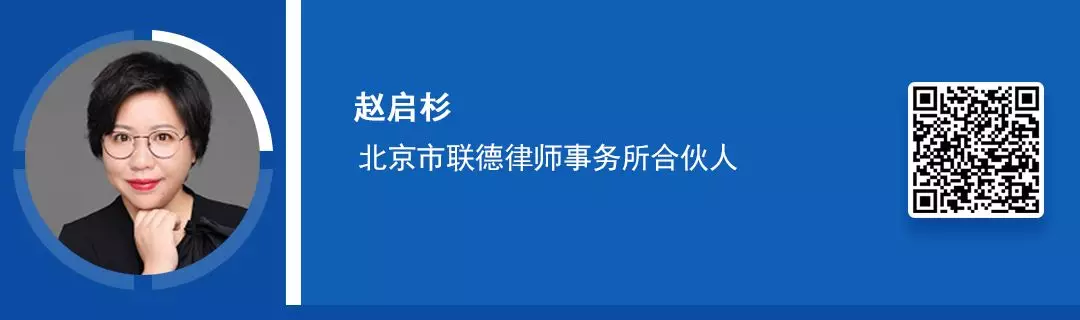联德知评 | 德国慕尼黑第一地区法院标准必要专利禁令救济指南介评
文 | 赵启杉 联德律师事务所
2020年2月,德国慕尼黑第一地区法院发布《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时反垄断强制许可抗辩适用指南》和《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时在言辞辩论程序内外处理保密申请的指南》。这两份指南是德国法院首次详细阐释其如何具体适用2015年欧洲法院在华为诉中兴标准必要专利侵权案裁判中所确立的负担FRAND许可义务的标准必要专利禁令救济规则,对德国法院在2015年以来在有关案件中的审判经验进行了总结,体现了德国慕尼黑第一地区法院对有关案件中关键性法律问题的倾向性意见,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2020年2月4日,德国慕尼黑第一地区法院发布名为《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时反垄断强制许可抗辩适用指南》的指南(以下简称禁令指南)。该禁令指南详细阐释了德国慕尼黑第一地区法院如何具体适用欧洲法院(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以下简称CJEU)2015年在华为诉中兴专利侵权案裁判中所确立的负担公平、合理和无歧视(fair, reasonable and non-discriminatory,以下简称FRAND)许可义务的标准必要专利(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以下简称SEP)禁令救济规则。该禁令指南对隶属于慕尼黑第一地区法院的两个专利法庭(第7和第21民事法庭)具有指导意义。[1]
该禁令指南共分为七个部分,着重就提起FRAND抗辩的前提条件、法院在负担FRAND许可义务的SEP禁令救济审查中如何对案件当事人FRAND许可谈判中的行为进行考察、案件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对负担的FRAND许可谈判义务如何进行补救、被控侵权人发起FRAND抗辩的前提条件以及案件双方当事人各自所负担的举证责任等内容进行了规定。另,关于在庭审中和庭审外如何向法院披露涉及第三方保密信息的可比许可协议的问题,慕尼黑第一地区法院单独制定了《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时在言辞辩论程序内外处理保密申请的指南》(以下简称保密指南),该指南也于2020年2月发布。
上述两份指南是德国慕尼黑第一地区法院对2015年以来其对有关负担FRAND许可义务的SEP专利侵权案件审判经验的总结,虽然不具有强制性的法律约束力[2],但是澄清了在有关案件审理中存在的争议性问题,体现了德国慕尼黑第一地区法院对SEP专利侵权案件审理中焦点问题的倾向性意见,因此对于在该地区法院有在审SEP专利侵权案件的当事人以及关注FRAND许可相关法律问题的研究者而言都具有一定参考意义。本文将就两份指南所涉及的重点法律问题结合有关规则的演变过程及典型案例分别进行介绍和分析。
一、关于FRAND抗辩的适用前提
德国法院对涉及SEP专利侵权的禁令救济问题采取的是将竞争法引入专利法的处理模式,即允许被控侵权人对SEP专利权人请求禁令救济的诉请提出抗辩,而如果德国法院认定SEP权利人拥有市场支配地位且因其拒绝向标准使用者许可其专利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时,则不支持该禁令救济。2009年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审理涉及事实标准的“橙皮书”案时构建了“强制许可抗辩规则” [3],而后德国法院又将该规则适用于对负担有FRAND许可义务的SEP专利侵权案件的审理之中,形成了所谓的FRAND抗辩。受此延续的影响,2015年德国杜塞尔多夫地区法院在就其审理的华为诉中兴SEP专利侵权案向CJEU请示时,仍然在竞争法框架下询问有关禁令救济的审理规则,而CJEU对该案的答复也并没有否定德国法院将竞争法引入专利法设置特殊抗辩规则的做法。
因此在禁令指南中,德国慕尼黑第一地区法院重申了SEP专利侵权案件中的被告提出FRAND抗辩的前提:(1)SEP专利权人拥有市场支配地位;(2)SEP专利权人或者其先前的转让人已向标准化组织作出过FRAND许可声明,即使涉案SEP曾被转让,该转让也不影响FRAND许可声明的效力。
需要注意的是,关于SEP专利权人是否拥有市场支配地位的问题,2015年7月CJEU在对华为诉中兴案的裁决中强调:《欧盟运行条约》(TFEU)第102条语境之下的市场支配地位是一个客观概念,而对知识产权人是否拥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判断必须基于个案案情判断。[4]近年来,德国法院也已经抛弃了所谓“拥有SEP必然拥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片面推论,[5]陆续作出了一些认定SEP权利人不拥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判决。例如,在France Brevets v. HTC案[6]中,原告FB是一项关于NFC专利技术的SEP排他被许可人,原专利权人参与了ETSI的LL标准的制定工作,并作出FRAND许可声明。原告起诉被告在德国销售的手机终端遵照LL标准实准支持通过手机终端SIM卡来实施NFC技术,侵犯了其SEP,并请求法院颁发永久禁令,而被告则提出FRAND抗辩。审理该案的杜塞尔多夫地区法院认为:第一,涉案标准所支持实现的移动支付功能并非是手机终端必须具备的基础功能,除非被告能够证明不具有这项功能的智能手机不能与具备此项功能的智能手机在市场上竞争,否则就不能认为该标准构成了市场进入壁垒;第二,本案中的LL标准支持智能手机通过SIM卡来实施NFC技术,而NFC技术还有另外两种可替代的实施方案。市场上也的确存在通过另外两种替代方案实施NFC技术的终端产品。被告也没有能够证明通过哪种方案实施NFC技术会影响到消费者的选择。因此最终杜塞尔多夫地区法院认定本案中标准必要专利权利人不具有市场支配地位,被告提出的FRAND抗辩无效,颁发了禁令。无独有偶,2018年6月,杜塞尔多夫地区法院在DTS-HD标准案[7]中的判决中总结了杜塞尔多夫地区法院、曼海姆地区法院和卡尔斯鲁厄高等法院的有关判决,再次强调:“市场支配地位意味着一种经济实力,即公司能够阻碍相关市场的竞争。为了使用一项技术标准而必须使用该专利这一事实本身并不能创设市场支配地位。事实上,该专利的必要性甚至都未能建立起一个法律上的假设,即该专利持有人可以凭该专利阻碍相关市场竞争”,“专利的标准必要性对于认定市场支配地位而言既不是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在该案件中,原告拥有的标准必要专利涉及ETSI的DTS-HD Master Audio标准。涉案专利所描述的技术方案需要由具备7个频道的HD解码器来实施,支持七个扬声器。而市场上还存在五个扬声器的HD接收器。专利权人并无法通过涉案专利阻止五个扬声器的HD接收器的市场销售,因此不能有效形成市场壁垒,阻碍竞争,从而被杜塞尔多夫地区法院认为不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综上,虽然慕尼黑第一地区法院在禁令指南中并没有明确规定如何分析判断SEP权利人是否拥有市场支配地位,但结合其有关条款文字表述和近几年来德国其他地区法院有关案件判决,可知在涉及SEP的专利侵权诉讼中,如果被控侵权人提出FRAND抗辩,德国法院将首先对SEP权利人是否拥有市场支配地位及涉案专利是否负担FRAND许可义务进行考察。
禁令指南在第二部分重申了CJEU在华为诉中兴案裁决中对FRAND许可谈判双方所负担谈判义务的规定:
2)标准实施者向SEP专利权人提出许可请求,该许可请求至少涵盖涉诉专利,标准实施者可以保留立即或稍晚质疑专利有效性和/或未侵犯拟许可专利的权利;
3)专利权人向标准实施者提供具体的、书面的FRAND许可要约,该要约至少涵盖涉诉专利;
4)如果SEP专利权人的要约未被接受:则应由标准实施者向SEP专利权人发出FRAND许可反要约,该反要约应至少涵盖涉诉专利,而标准实施者可以在该反要约中保留立即或者稍晚质疑专利的有效性和/或主张未侵犯拟许可专利的权利;
5)如果标准实施者发出的反要约未被接受:则标准实施者应该披露自己对有关专利的使用情况并提供担保;
6)双方未达成一致,可以在双方同意的情况下,选择交由独立的第三方来决定合适的许可费率。
在上述关于SEP专利权人和标准实施者所各自负担的谈判义务的规定中值得重点关注的有两点:
第一,德国慕尼黑第一地区法院在禁令指南中正式明确标准实施者可以保留质疑专利有效性和/或主张未侵犯拟许可专利的权利,这是德国法院首次明文否定之前德国法院对“橙皮书”案强制许可抗辩规则的有关阐释。按照德国联邦最高法院2009年在“橙皮书”案中的要求,被控侵权人(标准实施者)发起强制许可抗辩必须已提出无条件的、真实的、合理的和易于被接受的要约,而后德国法院在审理负担FRAND许可义务的SEP专利侵权纠纷案时援引橙皮书案规则,并将这一要求解释为标准实施人不可以质疑涉案专利的有效性。例如,2011年摩托罗拉公司在德国曼海姆地区法院起诉苹果公司侵犯其在欧洲拥有的标准必要专利,并同时请求法院颁布禁令阻止苹果公司在德国继续销售iPhone和iPad品牌下的相关设备。苹果公司则依据竞争法提出强制许可抗辩。但曼海姆地区法院援引“橙皮书”案判决,认为苹果公司之前向摩托罗拉公司提出的许可协议提案不能被认为充分满足了专利权人的正当权益,法院从而颁布了禁令。2011年12月9日苹果公司向德国卡尔斯鲁厄地区高等法院提起上诉,同时请求临时暂停执行初审判决,理由是:在地区法院判决之后,苹果又向摩托罗拉提出了修订协议建议。但2012年1月23日卡尔斯鲁地区高等法院裁定苹果关于许可协议的提案未包含具体条款说明苹果是否会在签订协议之后继续挑战相关专利的有效性,仍不满足“强制许可抗辩”条件。为此,苹果公司不得不再次修改许可协议提案,补充规定摩托罗拉可以在苹果公司挑战相关专利有效性的时候解除相关协议。据此,2012年2月27日高等法院认定苹果的建议已经提供了足以满足摩托罗拉合理利益的提议,并撤销了地区法院颁发的禁令[8]。德国法院的这种阐释受到了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的质疑。在2012年欧盟委员会在对摩托罗拉反垄断调查案[9]和对三星反垄断调查案[10]的公告中明确认为德国法院禁止标准实施者质疑FRAND许可谈判中SEP的有效性和必要性的观点是违反欧洲竞争法的。也正是对该问题看法的分歧直接导致了2015年杜塞尔多夫法院在审理华为诉中兴案时向CJEU请求就有关争议给与答复。对此,CJEU认为:鉴于标准化组织并未查验所谓标准必要专利是否有效或者是否真正“必要”,且被控侵权人亦有权获得有效的司法保护,因此被许可人(被控侵权人)在磋商过程中或者许可中质疑专利的有效性、必要性或保留质疑的权利都不应该受到责难。因此,在此次禁令指南中,慕尼黑第一地区法院正式明文规定标准实施者可以在其对侵权通知的应答和提出的反要约中保留质疑SEP有效性和主张未实施有关专利的权利,从而修正了之前德国法院在有关判决中的阐释。
第二,德国慕尼黑第一地区法院在禁令指南中要求SEP权利人在发出的要约中必须就以签订的可比协议情况和专利组合动态变化的情况给与解释。在禁令指南对第二条第三的进一步解释中,要求SEP权利人必须解释其报价、披露其是否已经与第三方签订了在许可期限和许可内容上具有可比性的协议以及在何种情况下签订该协议,并须进一步解释为什么其提出的许可要约涵盖了实施者所要求许可的专利之外的其他专利。在FRAND许可谈判中,对于标准实施者而言,SEP权利人与第三方已经签订的许可协议信息有助于其判断有关SEP专利组合的价值和衡量SEP权利人提出的要约是否合理。但是SEP权利人与第三方签订的在先协议可能会涉及一些敏感的商业信息,甚至可能包括受保密协议保护的商业秘密,强制要求SEP权利人在许可谈判向标准实施人披露其与第三方签订的可比协议又可能会损害第三方的合法利益。权衡之下,德国慕尼黑第一地区法院在禁令指南中只是要求SEP权利人在其所负担的保密义务允许的情况下提供有关信息,并就向法院和被控侵权人披露涉及第三方保密信息的可比协议的问题单独制定了保密指南。另外,在FRAND许可实践中,SEP权利人往往就SEP专利组合进行一揽子许可,而一则该SEP专利组合可能是动态变化的,二则该专利组合中可能包括标准实施人并未请求给与许可的专利。在CJEU华为诉中兴案的裁决和之后德国法院的相关判决中,较多强调的是SEP权利人在发出要约时要提供专利清单(或示例性专利清单)、示例性权利要求对照表[11]、负担FRAND许可义务证明以及许可费计算依据等信息。而此次禁令指南中,德国慕尼黑第一地区法院则进一步要求SEP权利人对专利组合中包含的非标准实施人所请求许可的专利权的必要性进行阐释。这代表了德国法院对FRAND许可实践中处于不断动态变化中的专利组合的关注。
三、言辞辩论结束之前对FRAND许可谈判中瑕疵行为的补救CJEU对华为诉中兴案的裁判不仅为欧盟各国法院确立了在涉及负担FRAND许可义务的SEP专利侵权诉讼中审查禁令救济的规则,也实际上为进行FRAND许可谈判的当事人树立了如何以诚信的态度进行谈判的指引。理想的情况是,当事人双方在完全切实履行了各项FRAND许可谈判义务之后仍无法消除分歧时才向法院提起有关诉讼,但在实践中,FRAND许可谈判因其复杂性往往持续数年,而在此期间法院关于FRAND许可谈判行为的要求在不断细化,所以可能出现当事人在起诉后发现其FRAND许可谈判中的行为不完全符合法院规定的情况。
对此,德国法院的一些判决认为应该赋予当事人弥补其FRAND许可谈判中过错的机会。例如,在DSL标准案[12]中,原告通过受让方式获得关于数据通讯标准ADSL2+和VDSL2标准的标准必要专利。原专利权人曾向制定这两项标准的ITU作出了FRAND许可声明。被告在德国向客户通讯服务,其业务包括使用ADSL2+和VDSL2两项标准向客户提供DSL连接服务。2016年1月原告向杜塞尔多夫地区法院提起针对被告的侵权诉讼,在起诉后,原告才两次向被告提供要约,被告也作出了反要约并就其使用标准必要专利的行为提供了担保,但是双方未能达成协议。该案发生在CJEU对华为诉中兴案作出裁判之后,因此按照CJEU在华为诉中兴案裁判中确立的框架,原告应该在提起侵权诉讼前向被告发出FRAND要约。但是审理该案的杜塞尔多夫地区法院认为应该给专利权人一定的空间允许其对未及时提供要约的行为进行补救,因为一则,即使在起诉之后,双方仍可能处于谈判之中;二则从诉讼效率角度出发,也应允许原告在起诉后根据被告的反要约情况在一定期限内“修补”其要约,使其要约更符合FRAND的要求。但是也有德国其他地区法院采取更为严格的要求,不允许SEP权利人在起诉后再发出FRAND要约。例如曼海姆法院认为CJEU强调当事人在没有受到诉讼压力的情况下进行FRAND许可谈判,而一旦标准必要专利权利人发起侵权诉讼,标准实施方就不能在无压力的情况下来考虑是否接受标准必要专利权利人的要约。如果标准必要专利权利人在提起侵权诉讼后发出要约(包括发出新的要约)就应该中止侵权诉讼程序允许另一方充分考虑是否接受该要约。[13]
权衡赋予当事人弥补过错尽一切可能促使双方尽快达成许可协议和同时确保有关案件审判司法效率的需求,德国慕尼黑第一地区法院在禁令指南中规定:当事人双方可以在首次庭前会议上确定自己在履行前述许可谈判步骤时是否有瑕疵,并利用首次庭前会议期日到开庭审理期日之间的这个时间段对其行为瑕疵进行补救。如果SEP专利权人向同一专利法庭同时针对不同标准实施者提起多项SEP专利侵权诉讼,则受理该系列案件的专利法庭应该组织一个不涉及技术事项的庭前会议,对这系列案件所涉及的FRAND抗辩事宜进行集中讨论。如果SEP专利权向两个专利法庭同时针对不同标准实施者提起多项SEP专利侵权诉讼,则受理该系列案件的两个专利法庭应该彼此协调有关FRAND抗辩事宜的讨论。
四、关于FRAND抗辩发起程序及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
禁令指南的第四部分是对FRAND抗辩程序的描述,其中最为核心的内容是关于如何发起FRAND抗辩程序及抗辩中双方当事人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定。
1.发起FRAND抗辩的前提条件
根据禁令指南第四部分第一条的规定,发起FRAND抗辩的前提条件如下:
(1)被告提起FRAND抗辩,且应尽早提出(建议在应诉答辩中就提出该抗辩);
(2)原告诉讼请求中申请了永久禁令,即原告在诉讼中至少主张了停止侵害、召回侵权产品以及销毁侵权产品三个请求权中的一个;
(3)前述FRAND许可谈判义务已被履行:对发起FRAND抗辩的被告而言即为,如果被告拒绝接受原告的要约,其须向原告发出了反要约(要约与反要约均需包含涉诉专利);而如果原告拒绝了该反要约,被告则应已披露了自己对有关专利的使用情况并提供了足额的担保。慕尼黑第一地区法院没有过多强调反要约的及时性,[14]而是侧重于对反要约内容的要求。按照禁令指南的规定,反要约首先不能是另一方完全难以接受的;其次,虽然反要约可以在许可期限或许可内容上对SEP权利人发出的要约进行缩减,但是必须包含涉诉专利,同时被告可以保留质疑有关专利有效性和主张未侵权的权利;第三,反要约中可以不包括具体的许可费率而是要求专利权人重新确定具体许可费率。上述三点要求中的第三点值得重点关注,其观点似乎与德国曼海姆地区法院的意见相反。在曼海姆地区法院审理的圣劳伦斯公司诉德国电信公司案[15]中作为第三方加入诉讼的HTC公司在拒绝接受原告的要约之后向原告发出反要约,但反要约中不包含具体许可费,而是提议由受理平行诉讼的英国威尔士高等法院裁判费率,而审理该案的德国曼海姆地区法院认为标准实施人的反要约未包含具体的许可费请求,不能被认为是符合FRAND许可原则的反要约。除提供内容完备的反要约之外,被告要发起FRAND抗辩还须注意在反要约被拒绝时及时披露有关专利使用情况和提供担保。关于担保的数额,禁令指南的规定是:如果被告在反要约中提出了具体的许可费率,则应以反要约中的许可费率为基准,披露并核算从首次适用起至一审判决作出之间适用相关专利的情况,计算出许可费并进行提存;如果被告未在反要约中提出具体的许可费率则有关许可费使用费的计算应以SEP权利人在要约中要求的许可费率为基准计算;如果有关FRAND许可是全球性的许可,则提存的数额按照德国市场营业额的110%进行计算。
(4)如果被告与专利权人之前已经缔结过FRAND许可协议,但因被告单方面的原因解除合同或者导致合同终止,则被告无权发起FRAND抗辩;
(5)如果SEP专利权人发出的要约中包含某项专利,而被告发出的反要约中未包含该专利,则被告不得就该专利主张FRAND抗辩。
2.FRAND抗辩中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
如前所述,德国法院采取了将竞争法引入专利法设立特殊抗辩规则的方式来处理负担FRAND许可义务的SEP的禁令救济申请的审查问题,因此禁令指南在关于FRAND抗辩举证责任的分配上规定提出FRAND抗辩的被告将就抗辩事项首先承担举证责任,而原告承担次级举证责任。
提出FRAND抗辩的被告承担的举证责任包括:
(1)证明FRAND抗辩的构成要件均已满足,特别是说明为什么原告最后一次提出的要约不符合竞争法和FRAND原则;
(2)如果被告没有发出反要约,则必须证明为什么原告上一次提出的要约在竞争法上是完全无法接受的,或者证明原告应该向被告供货商而非被告寻求许可;[16]关于原告应向被告供货商寻求许可的抗辩,禁令指南设置了限制性的条件,即如果被告本来可以与原告达成许可协议,且被告也可以将有关许可信息传递给其供应商,则只要能够确保专利权人不会获得双倍许可费,被告就不得适用此抗辩理由;
(3)如果原告向被告发出的要约中已包含合理、充分且具有追溯力的最惠待遇条款,而被告仍然对要约中所包含的许可费率不满意,则被告必须证明为什么该要约中的许可费率过高;
(4)如果被告主张在先许可协议是标准实施方在受到压力的情况下缔结的,则被告需要证明没有这种压力的存在时,双方会签订更低许可费或更优惠许可条件的许可协议;
(5)如果被告保留质疑拟许可专利组合中某些专利(非涉诉专利)的有效性或主张未实际使用相关专利、权利用尽和/或有关专利已经被许可的权利,且被告以此作为抗辩理由之一,则被告需要对这些抗辩理由负担举证责任并说明这些情况会对专利组合的许可费确定产生一定影响。
在FRAND许可抗辩中原告承担的举证责任主要包括:
(1)对其发出的要约承担次级举证责任,即如果有未公开的信息或者被告尚不之情的情况,原告须告知其之前是否与第三方签署过在许可期限和内容上具有可比性的许可协议并说明在何种情形下签订了该许可协议。如果涉案专利系经过转让所得,且有关可比协议是原权利人与第三方签订的,原告仍然需要承担该举证责任;如果涉案专利组合经过多次转让,法院可以根据个案决定原告此项举证责任的详细程度;
(2)如果被告提出涉案专利组合呈现动态变化,[17]则原告需要说明为何要将新的专利纳入该专利组合中以及纳入这些专利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许可费。如果原告在要约中已经表示愿意加入合理、充分且有溯及力的“调整条款”,以便将专利组合的动态变化情况纳入许可费考量因素之内,则被告不能再据此作为抗辩理由,原告也无需对此再承担举证责任。
五、关于在言辞辩论程序内外如何向法院披露涉及第三方保密信息的可比许可协议
如前文所述,禁令指南规定原告在FRAND许可抗辩中的举证责任主要是对其与第三方签订的可比许可协议及签订情况进行披露和说明。而在FRAND许可谈判中往往会涉及一些敏感的商业信息,因此谈判双方往往签订保密协议(NDA协议),相互约束禁止对外披露有关谈判或协议所涉及的敏感商业信息。但是可比许可协议无论是对于后续标准实施者分析要约报价还是对于审理有关纠纷案件的法院判断要约与反要约的合理性而言都是重要的参考依据,因此如何协调处理可比许可协议的提供与第三方商业秘密保护之间的关系成为摆在各国法院面前的难题。
首先,对于原告而言,可能会因为其与第三方签订NDA协议而对向其他标准实施人和法院披露可比协议存在顾虑。例如,在2019年8月德国慕尼黑地区法院审理的诺基亚诉戴姆勒SEP专利侵权案[18]中,被告的部分供应商作为第三人参加审理,其中一个供应商向法院请求查阅原被告向法院提交的所有证据材料却又拒绝与原告签订保密协议。原告遂以其证据材料中包含保密信息(如其与第三方签订的在先许可协议和其与被许可方之间关于谈判事项的往来邮件等)而请求法院拒绝该供应商查阅文件的请求。对此,审理该案的慕尼黑地区法院认为支持原告的保密请求需要满足以下前提条件:
(1)原告已经向法院提交了请求被考虑为保密信息的事项;(2)原告向法院提交这些保密事项是因为原告已经与被告签订了NDA协议;(3)诉讼参加人后来才加入诉讼之中;(4)原告请求拒绝披露这些保密事项是合理的;(5)诉讼参加人拒绝与原告签订NDA协议;(6)诉讼参加人拒绝签订NDA协议没有合理的理由。就该案而言,慕尼黑地区法院强调FRAND许可总体上要求有关许可条件的透明,因此FRAND许可协议除非能够证明其内容符合商业秘密的要求,否则一般不能认为具有保密性。对谈判双方的邮件也适用同样的规则。因此法院拒绝了原告关于不披露在先许可协议和往来邮件的保密请求,但是法院不要求原告披露证明这些许可条件合理性的细节信息。在该案中,请求披露方是否与原告签订NDA协议和有关信息本身是否符合商业秘密的实质性要件直接关系到原告披露的信息的范畴。
其次,披露在先许可协议可能会涉及到对第三方合法利益的保护问题,因此法院需要考虑在程序上设置一定的保护措施以确保对有关保密信息的披露被限制在有限的范围之内。例如,在杜塞尔多夫地区法院审理的另一起DSL标准案[19]中,杜塞尔多夫地区法院对案件审理中披露第三方保密信息设置了一些保护措施,例如:(1)请求披露保密信息的被告需要与原告签订NDA协议;(2)有关保密信息仅能被用于本案的审理;(3)保密信息仅能提供给代表被告参加诉讼的四位自然人(包括在后续诉讼中加入的专家);(4)这些接触保密信息的个人也负担保密义务;(5)如果被告对外泄密,则应向原告支付1亿欧元的违约金。
吸纳上述审判经验,德国慕尼黑第一地区法院单独制定了保密指南。保密指南所规定的核心内容主要包括两方面:
(1)关于诉讼当事人之间NDA协议的签订:按照保密指南的规定,如果一方当事人主张已签订的许可协议中包含保密信息,如无法院命令,不能提交该许可协议或根据该协议内容提交有关诉讼材料,则该当事人必须确保与另一方当事人和/或该案的其他诉讼参加人在庭外已经签订NDA协议,从而使得向法庭提交有关诉讼文件或协议成为可能。如果另一方当事人或者诉讼参加人无正当理由拒绝签订该NDA协议,则其不能主张掌握保密信息的当事人未履行举证责任,相应的掌握保密信息的当事人也无义务披露任何保密信息;如果是部分诉讼参加人拒绝签订NDA协议,则可以将该诉讼参加人排除在涉及该保密信息的程序之外,或者如果原告与该诉讼参加人的诉讼可与原告和被告之间的诉讼分离时,原告也可申请将有关诉讼程序分离。
(2)关于向法院提交保密信息的形式要求和证明要求:如果当事人需要请求法院在言辞辩论中对其所提交的涉及保密信息的诉讼材料的查看或者写入判决进行特别限制,则应该尽量将有关保密信息作为单独的附件向法院提交,并在其首页上以显著的方式加以注明,在其向法院提交的诉状中应将该单独附件列为参考资料,也不应直接援引该保密信息。另外,提出保密请求的当事人须向法院说明案件中涉及的哪些保密信息,为什么需要在案件提及该保密信息,需要对何人保密,保密原因(即说明为什么对这些信息给予保密的价值超过了对外披露这些信息的价值)、程度和保密措施持续时间。
六、推动案件当事人在规定期限内进行二次谈判就围绕FRAND许可发生的系列诉讼而言,赢得单个案件的胜诉并非当事人的主要目的,通过诉讼获得更有利的谈判地位、争取有利于的许可条件才是双方当事人的最终目标。因此,大量围绕FRAND许可的诉讼案件因诉讼过程中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而撤诉。从坚持私法自治和提高司法效率的角度而言,法院也希望双方当事人能够在诉讼过程中尽快消除分歧,达成合意,因此一些法院也尝试通过“二次谈判”机制(即法院组织之下双方再次谈判)来推动双方达成和解。[20]类似的,在德国慕尼黑第一地区法院的禁令指南中也规定:“诉讼双方应该充分利用首次庭前会议与开庭审理之间的时段,进行补充协商或者通过法院调解程序或者其他争议解决机制来寻求调解。”
七、关于在专利侵权案件中法院是否可以裁判FRAND许可条件的问题
在英国法院对无线星球诉华为SEP专利侵权案作出判决并裁定全球FRAND许可条件之后,有关法院是否可以在SEP专利侵权案件的审理中裁判全球FRAND许可条件的问题就引起了全球各司法辖区的广泛关注,而随着2019年10月底英国最高法院对无线星球诉华为案的二审判决和Conversant诉华为中兴案管辖权异议的二审裁定的再次开庭审理,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更是成为了目前FRAND许可有关法律问题中的焦点问题。
与英国法院将FRAND许可声明视为第三方利益合同,从而倾向于在合同法框架下解决有关FRAND许可争议不同,德国法院普遍认为FRAND许可声明仅在竞争法框架下的FRAND抗辩规则中具有法律约束力,并坚持在专利法框架之内审理有关SEP专利侵权诉讼案件。在此次慕尼黑第一地区法院发布的禁令指南中也再次表明了这种态度:基于对契约自由和私法自治的尊重,法院下辖的两个法庭将不直接规定有关合同条款的具体内容。
综上,德国慕尼黑第一地区法院在2020年2月发布禁令指南和保密指南旨在统一其下属两个专利法庭对SEP专利侵权案件的审判标准,并加快有关审理程序。按照禁令指南设计的审判流程,在理想的情况下,有关FRAND抗辩的问题将有望在第一次庭审时就得到解决。为确保两份指南的规则设计能有效平衡双方当事人的利益,2019年秋季德国慕尼黑第一地区法院为制定这两份指南向代表专利权人和标准实施者的两方律师、专利代理人和企业法务代表广泛征求意见,而就目前而言,代表专利权人利益和标准实施者利益的两方有关从业人员都对这两份指南给与了正面、积极的评价。
禁令指南和保密指南总结和吸纳了德国法院在2015年CJEU华为中兴裁决之后若干SEP专利侵权诉讼案件的审判经验,就SEP专利侵权诉讼案件审理中的一些法律问题进行了澄清和说明。就其具体规定而言,不少内容与我国法院发布的有关SEP案件审判指南的内容不谋而合。例如其关于双方当事人在FRAND许可谈判中各自应履行的谈判义务,就与北京高院2017年发布的《专利侵权审判指南》中第152条和153条的有关规定相近;又如,其关于允许当事人对FRAND许可谈判中的瑕疵行为进行补救的规定也与广东高院在2018年发布的《关于审理标准必要专利纠纷案件的工作指引(试行)》中考察当事人对过错行为的补救异曲同工;而其关于鼓励当事人在诉讼中补充协商或通过法院调解或其他争议解决机制达成和解的规定也与深圳中院在2018年华为诉三星案中组织的“二次谈判”秉承相同的理念。而该禁令指南和保密指南中的若干规定,例如其关于提起抗辩的被告应首先负担证明原告最后一次要约不符合FRAND原则的义务的规定以及关于向法院披露保密信息的前提条件和程序设计等对我国法院妥善处理SEP侵权案件中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和就可比许可协议设计举证妨碍规则等也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当然,该禁令指南和保密指南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例如禁令指南中未就法院对要约和反要约实质性审查的程度问题进行澄清,而关于这个问题德国法院在不同案件中的裁判尺度不尽相同;[21]又如保密指南中关于涉及第三方的保密信息的披露范围、程序等规定仍较为粗线条,特别是未在程序上赋予保密信息相关第三方就披露该保密信息提交意见和建议的权利。[22]就SEP专利侵权案件的审理而言,德国杜塞尔多夫地区法院和曼海姆地区法院审理的案件数量更多,其判决中有关法律问题的探讨更为深入。如果这两家法院随后也发布有关审判指南,则可以期待其作出更为详细和全面的规定。
注释:[1]https://www.juve-patent.com/news-and-stories/legal-commentary/new-frand-guidelines-from-munich-regional-court/,最后访问时间2020-02-20。据该新闻报道,促使慕尼黑第一地区法院在2020年2月颁布该指南的一个“催化剂”是,第7和第21民事法庭同时受理了诺基亚、夏普和Conversant诉戴姆勒汽车公司系列SEP专利侵权诉讼案,因此急需对案件中涉及FRAND问题的审理和有关禁令救济的审查规则进行协调。[2]两份指南所用德文原文为hinweise,意指对法院审判实践经验的总结。由于该指南不属于关于程序规则的正式司法解释,因此并不具有当然的法律约束力,一些德国律师对指南性质的解读为:“为进行SEP专利侵权诉讼的当事人提供了一种程序上的选择,即如果案件当事人同意法庭遵从该指南审理有关案件,则法院可以按照两份指南所规定的程序加快有关审理进程。”参见https://www.juve-patent.com/news-and-stories/legal-commentary/new-frand-guidelines-from-munich-regional-court/,最后访问时间2020-02-20。[3]See German Federal Supreme Court, 6 May 2009, KZR 39/06- “Orange-Book-Standard”. 在该案中,德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如果原告的专利已经成为进入相关市场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且原告的拒绝许可缺乏合理性和公正性,则被告可以适用强制许可抗辩。但同时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对提出强制许可抗辩的被告也提出了限制性的要求:1.被告已经向原告提出了无条件的(Unconditional)、真实的(Genuine)、合理的(Reasonableness)和易于被接受的(Readily Acceptable)要约,具体而言,被告提出的要约必须:(1)包含标的物、授权范围、签约双方、使用费等所有合同必备要素;(2)价格必须很高,高到如果专利权人再多要求许可费就将违反反垄断法,为保险起见,被告的要约出价必须达到或者超出FRAND许可合理许可费的上限,如果被许可人不能就合理的许可费做出判断则可以请求法院进行判断;(3)被告提出的要约不能以专利有效为条件、不能以证明实际存在专利侵权为条件;2.被告须预期履行(Anticipatory Performance)其合同相关义务,具体而言,(1)被告需要向原告提供其财务账单,以便原告查证被告使用其专利、获取收益的情况;(2)被告需要事先审慎而合理地判断原告可能要求的专利许可费,并在合理期限内准备足额的专利使用费;(3)将自己准备的专利使用费存于专门的托管账户上。[4] See Huawei v. ZTE, CJEU, 16 July 2015, Case C-170/13.[5] 2007年德国杜塞尔多夫地区法院在其审理的MPEG2标准案中曾持适用这种推论。参见LG Düsseldorf, Urt. v. 13.2.2007, Az. no. 4 a O 124/05 — Siemens/Amoi;LG Düsseldorf, Urt. v. 4.8.2011, Az. no. 47 4b O 54/10 — MPEG2-Standard[6] France Brevets v HTC,LG Düsseldorf,26 March 2015,Case No.4b O 140/13.[7] LG Düsseldorf,28.06.2018,Case No.4a O 23/17.[8] Motorola v. Apple,2012,Higher Regional Court of Karlsruhe,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Case No. 6 U 136/11.[9] European Commission. Antitrust: Commission Sends Statement of Objectionsto Motorola Mobility on Potential Misuse of Mobile Phone Standard-EssentialPatents[EB/OL],P1. (2013-05-06) [2013-07-19].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IP-13-406_en.htm.[10] European Commission. Antitrust: Commission accepts legally bindingcommitments by Samsung Electronics on 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 injunctions. [EB/OL],P3. (2014-04-29)[11]权利要求对照表的详细程度可视谈判双方是否签订保密协议而定。[12] OLGDüsseldorf,18 July 2017,Case No.I-2 U 23/17. [13] See IP Bridge v HTC,District Court of Mannheim,28 September 2018,Case No.7 O 165/16.[14]总体而言,关于反要约发出的及时性,德国法院会依据个案来判断。在NTT Do CoMo诉HTC案中,被告是在接到原告提出的要约一年半和有关诉讼发生半年之后才发出反要约的,而且在其反要约比标准必要专利权人拒绝之后未提供担保,其行为被认为构成“拖延谈判”。See NTT DoCoMo v HTC,LG Mannheim,29 January 2016,Case No. 7 O 66/15.[15] Saint Lawrence v Deutsche Telekom,LG Mannheim,Urteil vom 27.11.2015,2 O 106/14.[16]例如在圣劳伦斯公司诉德国电信公司案中,被告德国电信公司就主张原告应向自己的供货商——手机终端制造商寻求许可,而其供货商也作为第三人参与相关诉讼。See Saint Lawrence v Deutsche Telekom,LG Mannheim,Urteil vom 27.11.2015,2 O 106/14.[17]即较原告披露的可比协议而言,专利组合中所包含的专利数量出现了变化。[18] LG München,13 August 2019,Case No.7O 3890/19.[19] LG Düsseldorf,11 July 2018,Case No.4c O 81/17.[20]例如2018年我国深圳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华为诉三星SEP专利侵权案时就曾组织双方进行二次谈判。[21]例如在Sisvel诉海尔案(LG Düsseldorf, Urteil v.03. 11. 2015, 4a O 93/14.)中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在履行FRAND谈判义务上有明显瑕疵,因此颁布禁令救济,而二审法院认为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一审也仍需对原告要约是否符合FRAND进行具体分析;类似地,在DVD专利池标准专利侵权案中(OLG Karisruhe, Beschluss Vom 31.05.2016-6U55/16)二审法院也认为法院必须对要约进行全面深入的审视慎重考察期是否符合FRAND原则;类似的还有Pioneer诉Acer案(Pioneer v. Acer, OLG Karlsruhe,31 May 2016, Case No 6 U55/16)。但是有趣的是,尽管德国的一些高等法院一再坚持法院必须对权利人发出要约是否符合FRAND许可原则作出详细的计算和分析,但是该要求却受到了来自一审法院的抵制。例如在2016年曼海姆地区法院审理的NTT Do CoMo诉HTC案(NTT DoCoMo v HTC, LG Mannheim, 29 January2016, Case No. 7 O 66/15)中,曼海姆地区法院仍然认为:“即使标准必要专利持有人的要约略高于FRAND原则的门槛,也是符合欧洲法院要求的……如果标准必要专利持有人向实施者提供的要约的条件,在经济上远不如向其他被许可人提供的条件且没有客观理由,则不再认为其符合FRAND许可要求……法院只需要在简要评估的基础上,决定标准必要专利持有人是否违反了FRAND原则。”同样地,在2016年11月曼海姆地区法院审理的Philips v Archos案(Philips v Archos, LG Mannheim, 17 November 2016, Case No. 7 O 19/16)中,曼海姆地区法院仍然坚持认为“有权采取禁令的法院只需要在简要评估的基础上,决定标准必要专利持有人是否违反了FRAND原则。”[22]在TQ Delta公司诉ZyXEL案中,英国法院就赋予了保密协议所涉及的第三方对披露该保密信息提出异议的权利,并就保密信息的披露设置了专门的听证程序,以供法院审查在庭审中披露有关保密信息的必要性。See ZyXEL v TQ Delta,[2019] EWHC 562 (ChD),11 March 2019.
注:有关两个指南的具体中文翻译参见:
附件1:《慕尼黑州第一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时反垄断强制许可抗辩适用指南〉》,译者:魏立舟(德国慕尼黑大学法学博士)
附件2:《慕尼黑州第一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时在言辞辩论程序内外处理保密申请的指南〉》,译者:陆哲(北京联德律师事务所);校对:魏立舟(德国慕尼黑大学法学博士)
附件一:
慕尼黑州第一法院:
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时反垄断强制许可抗辩适用指南
(二〇二〇年二月版)
翻译:魏立舟(德国慕尼黑大学博士)
I. 适用范围
II. 概览:诉讼前双方就许可合同的协商必要履行的步骤
III. 言辞辩论结束之前对未履行步骤的补救
IV. 诉讼进程一览:
1. 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开始讨论反垄断抗辩
2. 在什么条件下可以于首次庭前会议即开始讨论反垄断抗辩
3. 在什么条件下可以要求将停止妨害、召回和销毁侵权产品请求权追加入诉
4. 对诉讼双方陈述的一些具体要求
V. 在言辞辩论程序内外对保密请求的处理
VI. 介于首次庭前会议与开庭审理之间的时段
VII. 合同条款
根据欧盟法院在“华为诉中兴”(案号:C-170/13)中所提出的原则,特制定本指南以规范慕尼黑州第一法院下辖的两个专利审判庭在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时对反垄断强制许可抗辩(以下简称“反垄断抗辩”)的适用。本指南的时间效力截止至更新的版本发布之前;除专利权纠纷案件以外,本指南亦同样适用于跟《实用新型法》和《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法》有关的案件。经法院事先通知,相关审判庭可以在具体个案中偏离本指南的规定。本指南的德语版本为官方版本。
【译者注】
a.本指南的发布单位为-Landesgericht München I,此处翻译为慕尼黑州第一法院。德国普通法院共分为四级,从低到高分别为Amtsgericht(初级法院)、Landesgericht(州法院)、Oberlandesgericht(州高等法院)和Bundesgerichtshof(一般可译为联邦最高法院)。关于Landesgericht的翻译,许多英文材料翻译为regional court,因此不少中文翻译将这级法院译为地方法院,但为了与Amtsgericht进行区分,建议直译为州法院更合适。
b.此外,慕尼黑州第一法院下辖的两个专利审判庭指第七庭和第二十一庭。
I.适用范围欧盟法院的“华为诉中兴”判决以及本指南的规定只适用于专利权人基于标准必要专利受侵犯而诉请停止侵害、召回以及销毁侵权产品的情形,只要该标准必要专利使权利人获得了相关市场的支配地位并且权利人或者其前手出让人已经向相关标准必要专利组织作出了公平、合理和无歧视的许可承诺(以下简称“FRAND承诺”)。该FRAND承诺不因专利权的转让而失效。至于其他情形,以欧盟法院的“IMS/Health”判决 (案号:C-418/01)和德国联邦最高法院“Standard-Spundfass”(案号:KZR 40/02)和“Orange-Book”(案号:KZR 39/06)判决为准。
II.概览:诉讼前双方就许可合同的协商必须履行的步骤根据欧盟法院在“华为诉中兴”中所确立的原则,本院认为在专利权人提起诉讼之前,专利权人和相关专利使用人双方应该完成如下步骤:
1)专利权人必须向使用人发侵权警告信,告知被侵权的标准必要专利以及具体的侵权行为(警告信中所指明的被侵权专利至少应包含嗣后诉争专利);
2)使用人必须向专利权人表达愿意就许可合同的缔结进行协商的意愿(许可意愿中至少应包含嗣后诉争专利),但就相关专利的有效性以及/或者使用人是否真实使用相关专利,使用人可以保留在今后对这些问题提出异议的权利;
3)专利权人必须向使用人提出一个具体的、书面的要约,该要约应符合FRAND原则(要约所涉及的专利中至少应包含嗣后诉争专利);
4)如要约未被接受:使用人必须向专利权人通过书面形式发出一个符合FRAND原则的反要约(该反要约所涉及的专利中至少应包含嗣后诉争专利),同样的,就相关专利的有效性以及/或者使用人是否真实使用相关专利,使用人可以保留在今后对这些问题提出异议的权利;
5)如反要约未被接受:使用人应该披露自己对相关专利的使用情况并提供适当担保;
6)双方未达成一致,可以在双方同意的情况下,选择交由独立的第三方来决定合适的许可费条件。
关于3) 专利权人有义务对其所提出的要约报价进行说明,并披露其在此之前是否已经与第三方签署过(在许可期限与许可内容上可相比较的)许可合同以及具体是以何种条件签订的这些合同;此外,在某些情况下,专利权人必须解释其为何将某些使用人并未要求许可的专利也一揽子地纳入要约报价。如果先前与第三方签署的许可合同就合同内容对专利权人课有保密义务,只要使用人签署了保密协议,专利权人——在合规的情况下——仍然可以将合同细节告知使用人。但是如果这样做仍不合规,专利权人则应在侵权诉讼程序中申请法院介入,就此可参考本法院制定的《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时在言辞辩论程序内外处理保密申请的指南》。[1]
III.言辞辩论结束之前对未履行步骤的补救根据《德国民事诉讼法》第136条第4款的规定,对于以上必要履行步骤是否按规定完成,应以言辞辩论结束为时点进行判断。根据本法院处理专利权纠纷的程序,该时间点即为开庭审理(Haupttermin)结束之时。因此,在遵循法律以及法院所设定的期限的前提下,具体缺漏的步骤必须在此时间点之前进行补救。根据本法院处理专利权纠纷的程序,只要具体缺漏的步骤最迟于首次庭前会议(früher ersten Termin)被确定,双方可以利用首次庭前会议与开庭审理之间的这个时间段对缺漏进行弥补。针对单个起诉,本院下辖的两个专利庭将——在可能的情况下——于首次庭前会议即处理反垄断抗辩,以给诉讼双方留出弥补缺漏的机会。在专利权人对不同使用人同时提起的多项诉讼由某一专利庭单独受理的情况下,该专利庭应该确定一个(不涉及技术事项)的庭前会议期日以集中处理反垄断抗辩。如果涉及同一反垄断抗辩的多项诉讼由两个专利庭分别受理,则两个专利庭应该彼此协调以求一致。
IV.诉讼进程一览:1. 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开始讨论反垄断抗辩
a) 被告主张反垄断抗辩;
b) 专利权人在诉讼中主张停止侵害、召回侵权产品以及销毁侵权产品三个请求权中的至少一个;
c) 被告——在专利权人向被告提出了一个许可要约(该要约至少包括了嗣后的诉争专利)且该许可要约未被接受的情况下——向专利权人提出了一个反要约(该反要约也至少包括了嗣后的诉争专利),且在反要约被专利权人拒绝后披露了自己的使用情况并提供了担保;
d) 如果被告与专利权人双方已经缔结了许可合同,但被告单方面解除合同或者因可归咎于被告的原因导致合同终止,例如被告迟延给付许可费,则被告无权主张反垄断抗辩;
e) 如果专利权人的要约中包括了某项的专利,但被告在提出的反要约中并没有包括该项专利,在这样的情况下,被告不得就该项专利再主张反垄断抗辩。
关于a) 被告应尽早提出反垄断抗辩,一般来说在应诉答辩中提起为宜。
关于c) 根据《德国民法典》第242条的诚实信用原则,专利权人在要约中提出的条件不能是另一方完全难以接受的。同理,被告在反要约中提出的条件也应符合这一条件。该反要约可以在许可期限和许可内容上进行缩减,但必须将(嗣后)诉争专利包括在内。同时,被告可以保留在现在或将来对被许可的专利主张无效或者提出未使用该专利进行抗辩的可能。此外,被告可以不在反要约中提出一个具体的许可费率,取而代之根据《德国民法典》第315条要求专利权人重新确定具体的许可费率。如果被告在反要约中提出了具体的许可费率,则被告至少要以其在反要约中所提出的许可费率为准,来披露并估算其自首次使用起至一审判决作出这段时间内使用相关专利的情况并对价款进行提存。如果被告在反要约中未提出具体许可费率,则被告应以专利权人在要约中提出的许可费率为准对使用情况进行披露并相应地对价款进行提存。如果诉讼双方的要约和反要约的效力及于全球市场,对使用情况的披露以及相关的提存数额以德国市场为限,一般要求按德国市场营业额的110%的数额进行提存。
【译者注】
关于《德国民法典》第315条的理解,参见罗歇尔德斯著,沈小军等译,《德国债法总论》(第7版),页边码240以下。
关于d) 此处还包括如下情形,双方先前缔结的许可合同中,就某些专利规定了对使用人有利的退出条款。如果使用人根据这种退出条款,就相关专利解除许可关系,那么使用人针对这些专利也失去了主张反垄断抗辩的权利,因为其以前已经获得了许可。
关于e) 同理,(如果专利权人在要约中包括了嗣后的诉争专利,但)被告在提出的反要约中并没有包括该项专利,那么被告针对这项专利也失去了主张反垄断抗辩的权利,因为可以理解为被告在这项专利上已经获得了专利权人的许可。
2. 在什么条件下可以于首次庭前会议即开始讨论反垄断抗辩
a) 原告在起诉时即提前对反垄断抗辩做了防御性的陈述;
b) 被告在答辩状中即主张反垄断抗辩;
关于a) 如果原告希望在首次庭前会议上就讨论反垄断抗辩,那么他在起诉书中就应该提前对被告可能提出的反垄断抗辩进行防御性陈述。对反垄断抗辩进行防御性陈述不以原告自始就主张停止侵害、召回和销毁侵权产品请求权为限;如果原告(在首次庭前会议上就事实和争点进行介绍之后以书面方式,或者在首次庭前会议上口头表示并最迟在首次庭前会议与开庭审理两个期日之间以书面方式)明确表示保留追加诉求的可能,对反垄断抗辩的防御性陈述也可以提前作出。在例外的情况下,例如事先不能预见被告会提出反垄断抗辩,则法院可以经申请给予原告在首次庭前会议之前进行补充陈述的机会。
关于b) 如果被告希望能在首次庭前会议即讨论反垄断抗辩,即使在原告还没有提出停止侵害、召回和销毁侵权产品的主张而仅将其作为备选项的予以保留情况下,被告也可以在答辩书中预先提出(防御性的)反垄断抗辩。
3. 在什么条件下可以要求将停止妨害、召回和销毁侵权产品请求权追加入诉
a) 原告如果有在之后追加新的请求权入诉的打算,可以在起诉书中以书面形式明确表示。原告最迟可以在首次法庭辩论以书面形式提出,或者在首次法庭辩论时口头提出然后在开庭审判期日之前以书面形式提出。
b) 因此而增加的需要预支的法庭费用以及/或者需要提供担保的诉讼费用应该尽快支付或提供。
c) 原告起诉主张信息披露、账目提供以及损害赔偿计算等请求权可以视为原告向被告发出了侵权警告信(诉前必要履行步骤1)。其他尚未履行的必要步骤必须在首次庭前会议日与开庭审理日之间进行弥补。受理专利权纠纷的审判庭根据具体案件的实际情况来设定补充履行的期间。如果原告在起诉书中已经对被告可能提出的反垄断抗辩进行了防御性的陈述,那么法院可以相应缩短弥补履行的期间。如果被告在答辩书中针对反垄断抗辩表明了自己的立场,那么审判庭可以直接在首次庭前会议上让双方就对涉及反垄断抗辩的某些问题进行沟通。
4. 对诉讼双方陈述的一些具体要求
a) 应当由被告方提出反垄断抗辩,被告必须陈述并证明反垄断抗辩的构成要件均已满足;这其中最重要的,被告必须说明为什么原告最后一次提出的要约不符合反垄断法(公平、合理和无歧视原则)的要求。
b) 在被告没有向原告提供反要约的情况下,则被告必须陈述并证明原告上一次提出的要约条件从反垄断法的角度看完全是无法接受的,或者原告本应许可被告的上游供货商使用相关专利(后者即所谓的“派生性”反垄断抗辩)。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被告本可以与原告达成一个许可合同,该合同将嗣后的权利用尽或者价值链内部的许可给予合理、充分并具有溯及力的考量,并且确保价值链的其他成员可以向被告披露相关信息的,“派生性”反垄断抗辩不成立。此外,必须确保专利权人不能通过主张损害赔偿请求权来重复收取许可费。
【译者注】
在专利权人与被告供应商对许可合同的内容签署保密协议的情况下,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可能会出现专利权人与某一产业链上下游公司就同一专利重复收取许可费的情况。但是根据权利用尽原则,这种情况下,原则上只能允许专利权人收取一次许可费。
被告如果可以证明,其专利权人基于反垄断法有义务许可被告上游供货商使用专利的,且上游供货商有意获得该许可的,那么即使被告不作出反要约,原告(专利权人)也无权主张停止侵害请求权。此即所谓的“派生性”反垄断抗辩。
但是此条规定认为在同时满足下面两个条件的情况下,这种“派生性”反垄断抗辩不能成立:一、原告的要约中包含了一个具有追溯力的“调整条款”,明确规定如果存在违反权利用尽规则的重复许可的情形,可以退还相应的许可费;二、原告允许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互相沟通相关许可信息,而不会违反相关保密条款的要求。
综合来看,此条规定目的在于说明,只要原告在许可合同的拟定时注意上述两个方面,被告就很难主张所谓的“派生性”反垄断抗辩。
c) 原告对其提出的要约承担次级举证责任,在相关信息未公开或者被告尚不知情的情况下,原告必须告知其在此之前是否已经与第三方签署过(在许可期限与许可内容上可相比较的)许可合同以及具体是以何种条件签订的这些合同。即使与第三方的许可合同是由诉争专利的前手出让人缔结,原告作为后手受让人仍然对此承担次级举证责任。在涉及多次转让以及/或者专利包的内容发生改变的复杂情形时,法庭可以根据个案情况来确定原告信息披露的具体程度。
d) 在原告向被告提出的要约中包含一个合理、充分并具有追溯力的最惠待遇条款的情况下(这种情况一般在专利权人首次许可时较常见),如果被告对该要约中的许可费率不满意,被告必须陈述并证明要约中许可费率仍然过高。如果被告主张之前的许可合同是被许可方在受到压力的情况下所缔结的,则被告必须陈述并证明如果没有这种压力的存在,双方会以更低的许可费率或者对被许可人更优惠的条件达成许可合同。
【译者注】
在首次许可中,为了打消被许可人的顾虑,专利权人经常会在许可合同中加入一个最惠待遇条款。如果签署了这么一个条款,专利权人有义务向该被许可人告知后续签约的情况,无论其与后续签约的第三方有无保密协议。此规定在于说明,即使有这么一个最惠待遇条款,被告仍然可以主张原告的要约条件高到完全难以接受,而拒绝对原告的要约作出反要约。
e) 若被告(在必要履行步骤的第2步和第4步中)针对专利包中的某些专利(非侵权纠纷中的诉争专利)保留提起专利无效申请、提起消极否认之诉(主张未实际使用)、主张权利用尽以及/或者相关专利已经被许可(以下统称“抗辩”)的可能,被告在侵权诉讼的过程中针对这些非诉争专利提出上述抗辩理由作为对抗原告诉讼请求的防御手段,在有争议的情况下,被告必须陈述并证明这些抗辩的成立。此外,被告必须陈述具体事实并且在有必要的情况下证明其抗辩所针对的专利对许可费用的确定具有一定的影响。如果专利包不是固定的,则以言辞辩论结束为时点,只有在此时点之前授予或公开的专利和专利申请可以成为被告提起抗辩的对象。针对被告的这种抗辩,原告承担次级举证责任,其必须说明为什么他要将这些专利放入专利包中,以及这些专利是否并且(如果是的话)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最后的许可费。如果许可合同的草案中包括一个合理、充分并具有溯及力的“调整条款”,规定被告若通过独立程序或在其他合同机制的框架下提起上述抗辩成立,就可以相应地退还许可费用,在这样的情况下被告就不能再在诉讼过程中将这些抗辩作为防御手段提出。
【译者注】
面对专利包中某些专利可能有问题的情况,使用人有两种选择:
一、事先排除
针对专利权人给的专利包中的专利,使用人可以选择事先排除一些他认为有效性存在问题或者根本没有使用的专利,这样这些被排除的专利自始不成为许可合同的一部分。专利权人针对这些专利可以提起侵权诉讼,使用人也可以提起无效申请。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使用人在败诉的情况下不能再主张反垄断抗辩,因此会有一定的禁令风险。
二、事后排除(加入调整条款)
针对专利权人给的专利包中的专利,使用人也可以选择一揽子接受,但是在许可合同中加入一个具有溯及力的“调整条款”。即规定,使用人可以单独提起无效申请以及不侵权之诉,在相关问题专利被无效或者法院判定不侵权的情况下,专利权人则有义务退还使用人针对相关问题专利之前已经缴付的许可费。这样对使用人的好处是,即使在败诉的情况下,仍然可以主张反垄断抗辩,从而避免禁令风险。
f) 如果被告针对主张专利无效、主张未使用诉争专利、主张权利用尽以及/或者专利已经许可,无论是在单独的程序中提起亦或——在可行的情况下——在反诉中提起,关于主张和举证责任的分配遵循一般原理。
V.在言辞辩论程序内外对保密请求的处理关于本院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时在言辞辩论程序内外对保密申请的处理请参见另外的指南。
VI.介于首次庭前会议与开庭审理之间的时段诉讼双方应该充分利用首次庭前会议与开庭审理之间的时段,进行补充协商或者通过法院调解程序或者其他争议解决机制来寻求调解。
VII.合同条款基于对合同自由和私法自治的尊重,本院下辖两个法庭要避免直接规定相关合同条款的具体内容。但是,合同条款的行文措辞必须切合个案实际要求,对双方利益进行合理平衡。在可能的情况下,可以参考第三方的模板进行起草。
[1]德语版请见:https://www.justiz.bayern.de/media/images/behoerden-und-gerichte/landgerichte/muenchen1/hinweise_geheimhaltung__stand_februar_2020_.pdf;英语版请见:https://www.justiz.bayern.de/media/images/behoerden-und-gerichte/landgerichte/muenchen1/guidelines_on_confidentiality_protection__stand_febr_2020_.pdf。
附件二:
慕尼黑州第一法院 [1]:
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时在言辞辩论程序内外处理保密申请的指南
(二〇二〇年二月版)
翻译:陆哲(联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
校对:魏立舟(德国慕尼黑大学博士)
本指南规定了慕尼黑州第一法院的两个专利审判庭[2]在审判侵犯专利权纠纷时在言辞辩论程序内外如何处理当事人的保密申请。在专利权纠纷及实用新型、半导体和补充保护证书相关指南更新之前,适用本指南。经法院事先通知,两专利审判庭在具体个案中可不适用本指南规定。本指南的相应德语版本为官方版本。
如果《德国专利法》(Patentgesetz,PatG)第145a条按计划生效(见《专利法简化和现代化第二部法案(草案)》(联邦司法和消费者保护部讨论稿)),则专利权纠纷应准用2019年4月18日的《德国商业秘密法》(Geschaftsgeheimnisgesetz,GeschGehG)第16至20条相关规定(见《联邦法律公报》(第一部分),第466页)。在此之前,适用以下规定:
如果一方主张,在缺乏相关保密措施的情况下,其无法陈述涉密的合同内容或提供该合同文本(例如,原告对其在要约中提出的报价承担次级举证责任,其必须披露之前与第三方签署的许可合同的内容),则在作出书面陈述之前,或提供合同文本之前,该当事人必须让另一方当事人和/或已参加此案的诉讼第三人在庭外签署保密协议,从而使书面陈述或合同文本提交成为可能。如果另一方不合理地拒绝签署保密协议,则承担举证责任的一方无需披露任何涉密内容。此时,由另一方承担举证责任,例如,证明权利人的报价构成反垄断法意义上的歧视,并且该方不能主张相对方未履行其信息披露义务。若后续有新加入的诉讼第三人,他们也必须签署庭外保密协议,否则,应适用2019年8月13日决定(编号:ECLI:DE:LGMUEN1:2019:0813.7O3890.19.0A)所规定的程序。
针对书面陈述的一些特定部分,如果要对查看文件和/或参与言辞辩论程序和/或写入判决进行特别限制,则应尽量将此类涉密信息作为单独的附件提交,并在其首页以显著方式注明。在书面陈述中,在提到此类涉密信息的地方应该隐去文字而备注相关附件信息。虽然可以备注相关附件信息,但必须确保书面陈述清晰易读。这种情况下,应适用《德国法院组织法》(Gerichtsverfassungsgesetz,GVG)第172条第2款的标准。根据相关规则,保密申请人必须向法院详细陈述、解释并使法院相信:需提及的涉密信息非常重要,以及在个案中保护这一秘密的价值超过公开审理这一公共利益。即使该案的其他当事人对该保密请求没有异议,本标准也同样适用。实际上,公开原则不在当事人的处分范围内。因此,建议当事人及时提交有事实依据的书面陈述,并强调何种信息对何人保密,以及保密的原因、程度和持续时间。
如果一方主张(例如,在提交已签订的许可合同文本时),由于这些许可合同中包含保密协议,若无法院命令,其不能提交这些许可合同文本或陈述合同的具体内容,在此情况下,该当事人必须及时说明这一情况,并根据《德国民事诉讼法》第142条请求法院颁发出示文书令。通常,两专利审判庭将接受该请求并命令出示该项文书,其中,文书出示令的颁发是基于另一方当事人和所有诉讼第三人已签署了庭外保密协议。如果该另一方当事人不合理地拒绝签署该协议,则该许可合同无需提交,如果诉讼第三人拒绝签署该协议,则在该保密信息范围内该诉讼第三人将被排除在后续程序之外。在适当情况下,例如,当原告与诉讼第三人针对的诉讼标的可分时,原告也可就此申请诉讼程序分离。
根据《德国商业秘密法》的规定,两专利审判庭的保密措施效力及于言辞辩论程序之外,该保密措施将从启动后持续至有证据证明(保密措施申请方)无权获得该保护时为止。在言辞辩论环节(及随后的判决)中,两专利审判庭将尽力避免讨论或提及涉密信息。如果必须要提及或讨论涉密信息且因此有必要决定将公众排除在外(从而不能接触到该信息)时,两审判庭均须审查申请排除的一方所提交的有事实依据的书面陈述,以判断是否满足排除公众的先决条件。
在制定出与《德国专利法》第145a条(计划颁布)相当的法律条款之前,本指南的暂行规定也适用于实用新型、半导体和补充保护证书的相关争议。
上述法律条款[3]生效后,对于进行中的诉讼,一方若要继续对涉密信息进行保密,无论是否已依据本指南暂行规定采取保密措施,均须依据《德国商业秘密法》第16条第1款立即请求法院作出裁决。
根据联邦法院于2020年1月14日作出的无线星球诉华为案判决(Akteneinsicht XXIV,案号X ZR 33/19)中的更为详细的规定,如果法院拒绝对一方所提交的特定书面信息采取保密措施,信息提交方可以将相关文件从已提交材料中撤回。该撤回的内容将不会提交给诉讼的其他各方,法院作出裁决时也不会考虑该撤回的内容。
基于对合同自由和私法自治的尊重,本院下辖两个法庭要避免直接规定庭外保密协议的具体内容。但是,合同的行文措辞必须切合个案实际要求,对双方利益进行合理平衡。在可能的情况下,可以参考第三方的模板进行起草。
[1]译者注:Landgericht München I也译为“慕尼黑第一地区法院”,为与附件1禁令指南的德语译本统一,本文采“慕尼黑州第一法院”这一译法。
[2]译者注:慕尼黑州第一法院下辖的两个专利审判庭是指第七庭和第二十一庭。
[3]译者注:指与《德国专利法》第145a条(计划颁布)相当的法律条款。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知产力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