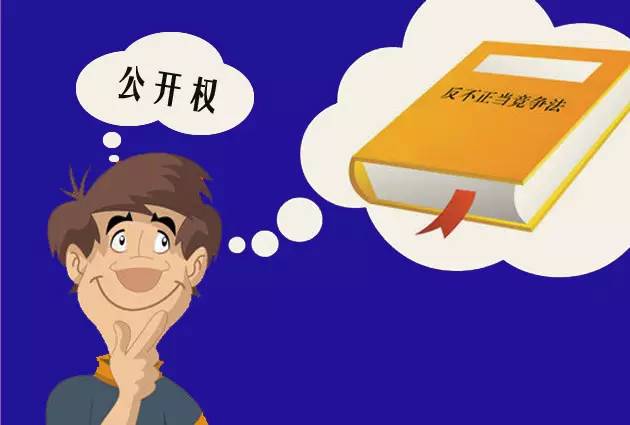从姓名权、肖像权到“公开权”——将“公开权”引入《反不当竞争法》的刍议(下)
知产力(微信ID:zhichanli)
知产力是一家致力于“为创新聚合知识产权解决方案”的原创型新媒体平台。关注科技领域创新及相关知识产权问题,请订阅本微信公众号(zhichanli)、官方微博:知产力,亦可登录www.zhichanli.com查阅更多精彩内容。
作 者 | 孙远钊
(本文系知产力获得独家首发授权的稿件,转载须征得作者本人同意,并在显要位置注明文章来源。)
四.引入“公开权”刍议
(一)中国的现况与需求
《民法通则》第99条规定,“公民享有姓名权,有权……禁止他人干涉、盗用、冒用”。第100条则规定,“公民享有肖像权,未经本人同意,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使用公民的肖像。”也就是把姓名权与肖像权限制在具有公民资格的自然人才可主张。而在之后的两个条文则规定了公民与法人的名誉权与荣誉权。在法规体系上这一系列的规定是放置在《民法通则》第四章(民事法律行为和代理)的第四节(人身权),但明显可以看出,关于肖像权的规定在性质上完全是财产权,而关于姓名权的规定则是两者兼而有之。
从1997年到2000年由鲁迅(周树人)之子周海婴所起诉的一系列《鲁迅肖像权》案,把逝者身后权益的问题首次推上了前台。虽然最终案件是以调解方式处理,但问题依然存在,尤其在既有的法规中实在难以找到适当的解决方案。[49]因此在2003年所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就对于逝者的肖像权作出了下列的规定:“自然人死亡后,其近亲属因下列侵权行为遭受精神痛苦,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一)以侮辱、诽谤、贬损、丑化或者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的其他方式,侵害死者姓名、肖像、名誉、荣誉;……”也就是确认了对逝者肖像应该予以法律保护。然而这项保护权的法律基础和具体的权益救济方案,则仍然一直难有定论。例如,非以营利为目的的使用肖像,是否仍会构成侵犯肖像权的阻却违法事由?由于目前绝大多数的讨论都还是集中在隐私权和人身(格)权方面,涉及到财产权的问题便一直延宕未决。[50]
此外,在最近发生的“德云社”相声师傅郭德纲与其徒弟曹云金之间的冲突事件,师傅是否可以单方、片面的禁止徒弟继续使用已经行之有年、带有辈份意义的艺名?如果该艺名还未申请商标注册,那么有了“公开权”的概念存在或将使整个问题的处理更加明确(该艺名就是专属于徒弟的财产权,不得任意遭人剥夺),但也可能产生新的问题(如果有商标注册,而权利人不是艺名所属的当事人)。[51]
在另一个引起了很大争议的68件《乔丹商标异议行政诉讼》系列案件,[52]最高人民法院已先后作出了50个行政裁定,驳回了异议人迈克尔·乔丹(Michael J. Jordan)的再审申请,维持了商标申请人乔丹体育公司所注册的“乔丹”、“QIAODAN”等系列商标为有效。法院认为异议人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争议商标的注册是以欺骗手段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即使争议商标损害了特定的民事权益(在此应是指乔丹的姓名权),也应当通过适用2001年《商标法》第41条(现行法(2013年)已变更为第44条)第2款、第3款和其他相应的规定进行审查判断,而不应纳入同条第1款(以欺骗或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调整的范围,因此一、二审法院适用法律并无不当。法院事实上就是支持了原审法院的观点,认为“乔丹”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英文姓氏,未必构成对商标的“唯一指向”、也未必在中国市场是被“广泛知晓”。不过已有论者认为这是过度僵化地适用地域原则和坚持姓名为人格权,却略了姓名的财产属性、市场竞争价值与优势所产生的结果。[53]
又如在《功夫熊猫商标异议行政诉讼》案,[54]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商标申请人在方向盘罩等商品上申请注册“KUNG FU PANDA”等商标应为无效,推翻了一审判决。二审法院的主要理由是,“当电影名称或电影人物形象及其名称因具有一定知名度而不再单纯局限于电影作品本身,与特定商品或服务的商业主体或商业行为相结合,电影相关公众将其对于电影作品的认知与情感投射于电影名称或电影人物名称之上,并对与其结合的商品或服务产生移情作用,使权利人据此获得电影发行以外的商业价值与交易机会时,则该电影名称或电影人物形象及其名称可构成‘商品化权’并成为商标注册中的‘在先权益’。”此一观点引发了许多的争论。[55]表面上的商标申请异议案件却浮现出了在底层现行立法的不足。设想如果此时有个完整“公开权”的概念与配套规制存在,那么就可以解除此处“司法造法”困境。但是受到保护的仍然是以自然人为限,所以在技术上最多只有扮演或对应该特定角色的演员才能提出主张,而且法院所应判认的关键是该演员与其所扮演的人物角色之间是否存在“难以分离的交织或纠结”,与观众对于电影作品认知的情感投射或是否对商品或服务产生了移情作用并无任何的关系。
由此可见,基于中国既有知识产权体系的发展情况与当前市场的强烈需求,将一个仍在持续演化之中、但已相当成熟的“公开权”概念引入已然成熟,也就是把既有的、关于姓名权和肖像权的财产权属性给正式、完全地彰显出来,并独立于既有的人身(格)权之外,原则上容许自由交易、转让,以释放出其背后的潜在市场力量与维权效益、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体系。
(二)具体立法可参酌事项
在具体的立法政策上,或可参酌《美国法律整(重)编:反不正当竞争(第三版)》(Restatement of Unfair Competition (Third),以下简称《法律整编》)的折衷立场,规定原告必须以具有相对较高盖然性的优势证据(preponderance of the evidence)举证被告未经许可取用了原告具有一定价值的身份识别信息以从事商业性的目的或活动,并导致原告受到损害。[56]立法者附带的还需论证思考制定相关的配套举措,包括:(1)是否需要制定回溯或逝者“公开权”的保护期间(目前的多数意见似乎是倾向于给予当事人死后10年的保护期);(2)逝者身后相关权利的转让、处置;(3)是否需要明文采用《转型使用》与《紧密纠结》等测试工具来做为司法平衡当事人的“公开权”与其他权益(包括知识产权)的基准;(4)是否需要对符合一定条件的特定类属个人推定具有一定的商业价值;以及(5)是否要把保护范围延伸及于由电脑生成的动画[57]或与剧中角色的对应等。
如果参酌加州等地的立法,则原告还需举证(1)被告是知悉而使用;以及(2)该使用与商业目的的关连性(意即被告对原告身份识别信息的使用是与其广告文宣或商业销售直接有关)等两个要件。[58]此外,由于过去尚无足够的成例,如何规制媒体或企业(法人)的新闻与商业言论自由范围也是必须进一并探索的课题。例如,印第安纳州的法律就明文排除了让“公开权”可以适用到文艺作品以及具有政治或新闻价值的材料等。[59]
(二)司法审查可参酌事项
法院在审查原告是否具有应受保护的“公开权”时,首要的考量是当事人(自然人)是否具有一定商业价值的个人识别以及被取用的身份识别是否可以获得保护。在举证方面,原告并不需要证明自己具有某种“名人”的身份,但必须举证其个人身份或信息具有某种显著性或是在相当范围内具有一定的知名度。至于是否要纳入当事人曾经试图利用自己的个人识别从事商业性的开发做为前提则是属于立法政策的取舍问题,应交由立法部门来讨论定夺。至于特定的信息是否可以受到保护,其中的主要考量在于被取用的信息与当事人的个人身份识别之间是否产生或具备了合理关连性(类似于商标法的“第二含意”secondary meaning)。
在审查是否构成“商业性的使用”时,并非纯粹的以是否为“营利性”做为依据(因为即使是公益性的活动也不可能都只是亏本运营)。[60]另一个(但不是唯一)可能的考量关键是,被告在其物件上所使用,关于原告的姓名、形象或肖像等个人识别信息其主要的目的是否在于从事与该个人信息以外的、属于物件本身独特的功利信息的传递(效应论或目的论)。[61]这也就意味著在诸如一般的书籍、期刊杂志与报纸等传统媒体上的使用基本上不至于产生对“公开权”的侵害。
由于“公开权”是可以客观超然存在的完整独立权利(in-gross right,亦即权利与实物载体得以完全分离),性质上是财产权,因此在政策上应尽量尊重契约自由的精神,采取鼓励自由交易和转让的立场,以便市场能够自行充分取舍运用。另外从概念上而言,虽然“公开权”与商标权在一些地方有些类似,但是两者之间还是有著根本上的区别:商标侵权原则上是要检视被指控侵权的标章是否对于权利人的商标有构成混淆的可能(之虞);而对于“公开权”的侵害则是要检视是否发生了盗用或未经许可使用他人的身份识别以获取商业上的利益,因此完全不问对于原告的身份识别是否有构成混淆的可能。[62]
(三)损害救济可参酌事项
对于侵害“公开权”的具体救济途径,基本上还是依循传统上的禁令(诉前保全或暂时禁令与诉后的永久禁令)与(金钱)损害赔偿两个面向。
在给予禁令方面,《法律整编》根据美国历来的司法判决归纳出了八个可供法院审酌权衡的主要参考因素以做为是否适合给予禁令的基础以及应涵盖的范围(但并不以此为限),相当具有借鉴价值:[63]
(1)受保护利益的性质;
(2)被使用或取用的性质与程度;
(3)禁令相与其他救济途径对原告的相对合适性;
(4)禁令给予与否对双方合法利益所可能造成的相对损害;
(5)第三方或公众的利益;
(6)原告的维权起诉是否有不合理的延宕;
(7)原告方面是否有任何相关的不当行为;以及
(8)将禁令的内涵予以具体化和执行的实效性。
由于涉及“公开权”的侵害通常范围是相对局限,除非另外涉及对于其他隐私权的侵害,禁令的范围一般就是禁止对于原告的个人识别从事未经许可的广告促销或其他商业性活动。如果原告曾经同意对其人身识别从事商业性的使用,那么禁令就只针对超越其许可范围的部分而发。至于禁令的地理或空间范围(包括网络空间)则应视个案的情形而定。由于法院必须平衡被告的言论自由,因此禁令的范围原则上不应太过广泛。[64]
在损害赔偿方面,《法律整编》所列示的基本原则是从原告所受到的损害或被告所得的利益之中选择金额较高的做为赔偿的基准,除非法律另有禁止规定或是权衡下列的六个因素后认为金钱救济并不适当:[65]
(1)原告举证被告使用对其所造成的损失金额与范围的可靠性;
(2)被告使用的性质与范围;
(3)相较于对原告其他救济途径的适当性;
(4)行为人(被告)的意图以及是否知悉或应知其行为构成不法;
(5)原告的维权起诉是否有不合理的延宕;以及
(6)原告方面是否有任何相关的不当行为。
需要指出,虽然 “公开权”的侵害并不局限于被告的故意行为,被告的意图或过失程度则与损害赔偿金额的确定息息相关(如果涉及故意侵权,法院还可依循一般侵权责任的法则对被告科以相应的惩罚性赔偿punitive damage)。对于一个相对次要的侵权者而言(例如涉及销售原告图像的小型零售商),往往以诉前保全或禁令便可构成合适的救济。此外,美国的法院有时会依据一般的侵权责任与民事诉讼规则要求被告让第三方(独立的会计机构)从事审计稽核,以追踪、确定其未经许可使用的所获利益,这一方面往往足以形成对被告的一种震慑或吓阻,另一方面也可比较确定被告获利与原告损失之间的对应关系,避免让原告从中牟取暴利。[66]
此外,鉴于具体的损失或是获利数额往往并不容易从双方的举证当中确定,法院经常会依赖专家证人的证词来评估被告不法使用的“公平市场价值”(fair market value, FMV)为何,例如合理许可费究竟应当为何等。此时诸如原告的相对知名度以及过去类似使用的收益等都可以做为辅助性的参考或依据。[67]
五.结论
虽然名称或有不同,“公开权”或与其类似类似的概念在欧、美、日等地已行之有年,并且发挥了相当的功效,值得参考借鉴,而且目前时机已然成熟,或许正可藉由《反不正当竞争法》准备进行23年来首次修改的机遇正式认可这个“琵琶遮面”了已久的权利。[68]
但必须特别指出,“公开权”只是做为完善知识产权体系的其中一块拼图(确立与个人识别信息相关的财产权),并不是万灵丹。这个权利的导入只是做为平衡不同权益之间的一项重要工具,因此固然可以一方面有效处理目前已经困扰了司法多时的法规不足问题,但在另一方面却也会让诸如著作权等其他排他性的知识产权未来的维权行使增加了潜在的变素而益形复杂化,甚至不排除成为阻碍知识产权自由行使、转让的障碍。因此,在相关的立法便尤其需要谨小慎微,在立法的说明中也应尽量的明确每个条文订立的宗旨,尽可能的确立其中的概念与各种要件的定义,从而法院虽然还是必须依据个案来从事认定,至少是在一个严谨的框架之中从事,并且避免将《反不正当竞争法》里的一般性或兜底性条款不当的扩张适用,导致造成市场的混乱或产生“寒蝉效应”。归根结底,“公开权”一般而言是个范围相对有限的排他性财产权,在与其他的权利行使产生竞合时,法院必须权衡各项不同的因素来寻求一个妥适的处理方案。此次对于《反不当竞争法》的修改,实有必要把此一概念正式予以规制,从而让整个知识产权与隐私权保护的体系更臻健全。
全文完
注 释:
[49] 于1988年1月26日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39点规定:“以营利为目的,未经公民同意利用其肖像做广告、商标、装饰橱窗等,应当认定为侵犯公民肖像权的行为。”不过这项规定仍然比较简单,没有把相关的举证推定与配套一并纳入考量。
[50] 张文信,浅析我国审判实践中对死者肖像权的保护,广西自治区贵港市港北区人民法院,2012年3月5日,http://ggzy.chinacourt.org/public/detail.php?id=782(作者在结论中表示,“我国当前的死者肖像权法律体系有着历史的沉病,立法技术不成熟的漏洞,不够精细和全面。并且和国外相比,我国只能称之为有限保护,在相关条文的理解和适用上,已经形成了只有“营利性使用”才能构成侵犯肖像权的所谓定论”);另参见罗豪才、孙琬钟编辑,《人民法院案例与评注:损害赔偿 (上)》,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页2-349至2-351。
[51] 另参见尚阳,郭德纲曹云金艺名之争:法学专家称更多属于“注册者”,《中国网》,2016年9月8日,http://news.china.com.cn/txt/2016-09/08/content_39259050.htm。
[52] 最高人民法院(2015)知行字第335号行政裁定书(2015年12月29日)。
[53]陈明涛、杜丹、朱龙臻,公众人物姓名权是知识产权吗?—对“乔丹”商标系列案的评析,2015年4月10日,兰台知识产权,http://www.huochai.mobi/p/d/170594/?share_tid=86291e50e9f4&fmid=0。
[54] 同前注3。
[55] 例如,刘迪,浅析“商品化权”的保护—以“功夫熊猫”商标权案为切入点,《东方知识产权》第47期,2015年9月。
[56] Restatement of Unfair Competition (Third) §§ 46-49 (1995).
[57] 孙磊,“公开权”是啥权利?—从《侠盗猎车手5》系列诉讼说起,《知产力》,2016年3月24日,http://www.zhichanli.com/article/27776。
[58] California Civil Code § 3344.
[59] Indiana Code §§ 32-36-1-1(c)(1)(A)-(B), 32-36-1-1(c)(3).
[60] “营利性”与“非营利性”的差别,并非等同于“赚钱”或是“不赚钱”,毕竟没有理由要求慈善机构等都必须亏本运营,否则势将无以为继。两者的差异是,营利涉及入股分红,而非营利则无。因此诸如学校与基金会等教育慈善机构都不得发行如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其决策通常是交由一个理事会(与董事会有所区别)的工作人员就是定期支薪(加上偶或有绩效奖金等)。
[61] McCarthy on The Right of Publicity and Privacy § 7:22 (2d ed. 2014)(“Where an image is used in connection with an article which serves primarily some intrinsic utilitarian function distinct from conveying information, then use of the image is commercial.”)
[62] 同前注7,页367。
[63] See supra note 56, § 48.
[64] Id., comment c.
[65] Id., § 49.
[66] Id., comment c.
[67] Id., comment d.
[68] 例如,法国和德国都是称为 “人格权”(right of personality)。参见《德意志共和国基本法》(Grundgesetz für 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第1条、第2条;德国《民法》(Bürgerliches Gesetzbuch, BGB)第823条第1款和德国最高法院(Bundesgerichtshof)在Marlene Dietrich Case, BGH 1 ZR 49/97 (1 December 1999)案的判决以及法国《民法》(Code civil)第9条。欧洲联盟基于大陆法的传统是一向从对于基本人身权利给予保护的立场出发,因此相关的规定可以与《欧盟基本权利宪章》(Charter of Fundamental Rights of the European Union)第3条关于保障人身自主权的规定完全接轨。唯有英国基于其历史传统,迄今尚无正式相关的立法。凡是想采取保护的当事人往往只能以诸如假冒(passing off)或破坏信赖关系(breach of confidence)等做为替代性的主张,但显然与“公开权”的概念并不契合,也从而招致了相当的批判,认为远远跟不上时代。参见Gillian Black, Recent Developments in Publicity Rights in the UK: Where Now for Celebrities?, contained as VI., Part B in Hugh H. Hansen, ed.,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and Practice (vol. 11)(2010), at 4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