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动了你的种子?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的5个核心问题
编辑 | 赵奕 路盛律师事务所
编辑 | 玄袂
都说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因为一粒微小的种子里蕴藏着隐秘的基因密码,这种密码能够将一颗优良种子的特征特性代代相传,继而繁衍出大量优质的粮食、果蔬、苗木。广袤的土地宽厚地涵养着每一个耕种者,但是播种下不同品质的种子或扦插下各异的枝条,土地给与的反馈可能天差地别。民以食为天,从市场的角度看,消费者总是愿意为更软糯的粳米、更甜美的苹果、更婀娜的盆栽支付更多的费用。因此,新颖的植物品种、带有优良特征特性的种子,是农业振兴的不竭动力,需要像初萌的新芽一样被悉心保护。那么当谈及植物新品种的保护时,品种权人最关心的莫过于:保护什么?怎么保护?如何定性?怎样计赔?能否停止侵权?笔者在此结合法条及案例,试回应上述问题。
01
保护什么?
要实施保护,首先要明确保护对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第二条明确:“未经品种权人许可,生产、繁殖或者销售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或者为商业目的将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重复使用于生产另一品种的繁殖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侵害植物新品种权。从上述规定不难看出,植物新品种的保护,在于保护“繁殖材料”。
那么什么是“繁殖材料”,一株植物上的各个部分均可以作为繁殖材料进行保护吗?我国的相关法律和行政法规对于繁殖材料进行了列举式地介绍,但是并未给出明确的判断标准来判定哪些属于繁殖材料哪些不属于。例如,《种子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种子,是指农作物和林木的种植材料或者繁殖材料,包括籽粒、果实、根、茎、苗、芽、叶、花等”;但是,一株植物的上述部分未必都能稳定地传递该品种的特征,即保持植物新品种授权条件中的“一致性”。事实上,只有那些经过种植,在代际繁殖中保持高度“一致性”,繁殖出的新个体的特征特性与原品种特征特性相同的部分,才能够被认定为繁殖材料。
虽然,“细胞全能性学说”认为“植物器官和组织可不断被分割,直至单个细胞;在经过体外培养后具有形成完整植株的能力”。但该学说在目前的生物技术条件下尚不足以论证某品种植株的所有部分均为繁殖材料。一方面,非活体细胞(如导管细胞)和无核细胞(如筛管细胞)显然不能通过培养形成完整植株,主要由上述细胞组成的部分显然不能被认定为繁殖材料;另一方面,细胞的体外再繁殖过程受到诸多外部因素(特别是细胞变异可能性和退化程度)的影响,不是所有植株部分均能形成相同特征特性的新的完整个体。
在“三红蜜柚”案中[1],法院认为“判断是否为某一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 在生物学上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其属于活体, 具有繁殖的能力,并且繁殖出的新个体与该授权品种的特征特性相同。被诉侵权蜜柚果实是否为三红蜜柚品种的繁殖材料, 不仅需要判断该果实是否具有繁殖能力, 还需要判断该果实繁殖出的新个体是否具有果面颜色暗红、 果肉颜色紫、白皮层颜色粉红的形态特征, 如果不具有该授权品种的特征特性, 则不属于三红蜜柚品种权所保护的繁殖材料···对于三红蜜柚果实能否作为繁殖材料, 经审查, 即便专门的科研单位, 也难以通过三红蜜柚果实的籽粒繁育出蜜柚种苗。二审庭审中, 蔡新光所请的专家辅助人称, 柚子单胚, 容易变异, 该品种通过枝条、 芽条、 砧木或者分株进行繁殖, 三红蜜柚果实有无籽粒以及籽粒是否退化具有不确定性。综合本案品种的具体情况, 本案被诉侵权蜜柚果实的籽粒及其汁胞均不具备繁殖授权品种三红蜜柚的能力, 不属于三红蜜柚品种的繁殖材料。”该案例很好地诠释了在个案中认定繁殖材料的标准,丰富了繁殖材料的内涵,即只有品种植株“活体, 具有繁殖的能力, 并且繁殖出的新个体与该授权品种的特征特性相同”的部分才能被认定为繁殖材料。
深入来看,在上述三要件中,“新个体与该授权品种的特征特性相同”是最核心的要素。那么,在个案中,如何确定“特征特性相同”,是否也需要以类似“田间观察”的方式进行验证?“田间观测”费时费力,在每一个案件中以此方式确定繁殖材料显然会大大拉长审理期限;笔者认为,考察该类品种业内通用的种植方式以及观察该些种植方式所用之材料(特别是品种权人和涉嫌侵权人所采用的种植方式和选取的材料)不失为一种方法。因为业内通用的种植方式和所选材料是经过科学实验和种植实践所筛选出的最优选的生产方式,所选择的植株部分显然是最有利于表现该品种性状、特点和特征特性的。而无论是品种权人还是涉嫌侵权人,在利用某一植物新品种进行繁殖时,都会在长期种植实践中累积丰富经验,精心选用最能保持品种一致性的植株部分进行繁殖(种植),力求繁殖出的新个体能最大程度地表达该品种的优越特性。以苹果为例,业内常用的栽培方法之一是将“强壮有活力”的苹果枝条作为接穗,嫁接于“靠谱”的砧木上,从而获得完全表现接穗性状的苹果树,进而收获果实。那么,通过考察业内通用种植方式和所选材料,可以较快捷地认定苹果的枝条部分是一种繁殖材料的。
当然,回顾“三红蜜柚”案,即使假设三红蜜柚的籽粒能够繁殖出相同特征特性的完整蜜柚植株,该案中在电商平台销售三红蜜柚的销售者亦不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二)》(以下简称“若干规定二”)第九条,“被诉侵权物既可以作为繁殖材料又可以作为收获材料,被诉侵权人主张被诉侵权物系作为收获材料用于消费而非用于生产、繁殖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本案中,该三红蜜柚显然具有食用功能和消费属性,销售者当不难举证其在网店销售三红蜜柚是为了用于消费而非帮助购买者进行再繁殖;即使有个别生物爱好者食用后种植,也当属于“私人非商业性行为”,因此三红蜜柚并非繁殖材料而是收获材料。进而,既然三红蜜柚果实并不认定为法律意义上的繁殖材料,那么销售该三红蜜柚自然也不构成侵害植物新品种权。
可见,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中第一个要解决的是回答“保护什么”这个问题。与专利不同,植物新品种不具有可以用权利要求文字清晰描述和划定的“保护范围”,而是需要在每一个个案中针对不同的植物类型和品种,审慎确定。如果繁殖材料把握不准,则整体的侵害植物新品种权之诉将会成为无本之木。
02
怎么保护?
确定了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范围(繁殖材料)后,就可以针对该繁殖材料进行有针对性的保护。我国法律和司法解释通过禁止一系列针对植物新品种繁殖材料实施的特定行为,对其进行保护。这些行为包括早期保护条例中规定的生产、销售行为,也包括近期司法解释中规定的繁殖、重复使用生产另一种繁殖材料,以及明知他人实施侵害品种权行为仍实施收购、存储、运输、以繁殖为目的加工处理、提供相关证明材料。针对植物新品种繁殖材料实施上述明确列举的行为将被认定为构成侵害植物新品种权。同时,另外一些行为也值得特别关注。
第一,许诺销售(繁殖材料)行为可以在个案中被拟制为销售。“若干规定二”明确“以广告、展陈等方式作出销售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的意思表示的,人民法院可以以销售行为认定处理”。众所周知,知识产权案件的取证普遍比较困难, 特别是追溯专利侵权案件和植物新品种侵权案件中的侵权源头,往往对权利人的取证工作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在《专利法》中,许诺销售行为被单独列为一种侵权行为,即如果行为主体仅实施了对被控侵权产品的宣传推广作出要约的意思表示,就可以被认定为构成对于权利人专利权的侵害。在植物新品种案件中,对于许诺销售行为可以直接以销售论处,大大扩展了对于植物新品种的保护网;特别是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权利人的举证负担,因为大量侵权人在销售繁殖材料时都只发布销售品种的信息,而真正的繁殖材料一般隐藏得十分隐蔽,对于销售行为的取证难度远高于对于许诺销售行为的取证。
事实上,许诺销售行为被认定为直接侵权行为也符合《UPOV 1978年文本》的条约规定。 我国于1998年8月加入UPOV (1978年文本),其中第5条明确规定 “The effect of the right granted to the breeder is that his prior authorization shall be required for the production for purpose of commercial marketing, the offering for sale, the marketing of the reproductive or vegetative propagating material, as such, of the variety. ”。因此,在植物新品种案件中对于许诺销售行为予以规制,既有切实拓宽植物新品种保护网络的现实需求,也符合我国所加入国际条约的精神。在“金粳818”案件中[2],二审法院认定“销售合同成立前的广告、展陈等行为已足以认定为销售行为,销售者是否亲自实施标的物的交付和收款行为,不影响其销售行为性质的认定。亲耕田公司实施了发布被诉种子销售具体信息,与金地公司取证人员协商确定种子买卖的包装方式、价款和数量、履行期限等交易要素,其行为对于被诉侵权种子的交易不仅具有肇始意义,而且金地公司依据与亲耕田公司约定的交易条件,已产生据此取得被诉侵权种子所有权的确定预期,销售合同已经依法成立。可见,亲耕田公司系被诉侵权种子的交易组织者、决策者。后续交易履行过程中货物交付和收款的主体的变化,并不影响认定亲耕田公司的销售主体地位。故根据上述事实,可以认定亲耕田公司直接实施了被诉侵权种子的销售行为”。在该案件的裁判中,可以清楚看到,虽然被控侵权的新品种繁殖材料“金粳818”并非直接来源于亲耕田公司,但其所实施的发布该种子的销售信息、就销售细节进行磋商等许诺销售行为被评价为销售繁殖材料的侵权行为。
第二,种植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的,可以个案认定为生产、繁殖行为。种植行为能否被评价为侵权行为,司法实践中存在过不同的意见。2016年山东高院再审的“美人榆”案件中[3],山东高院认定“美人榆系无性繁殖,本身即为繁殖材料,九台园林处大量种植美人榆用于街道绿化的行为不符合《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第十条规定的可以不经品种权人许可而不支付使用费的情况。九台园林处没有从品种权人处购买美人榆,而擅自进行种植使用,其行为暗含了商业利益,损害了品种权人的权益,应当认定为具有商业目的···所以,九台园林处擅自种植美人榆的行为侵害了涉案植物新品种权。”而在2018年的“美人榆”案件中[4],最高院再审认定“本案无证据显示衡大管理处种植涉案美人榆苗木是为了销售营利,且其并未实施扦插、嫁接等扩繁行为,在此情况下,种植行为本身既不属于生产行为,也不属于繁殖行为。同时,衡大管理处的相应种植行为亦不受品种权中销售权能的调整。此外,单纯的种植行为也不属于种子法上规定的“将授权品种繁殖材料重复使用于生产另一品种繁殖材料”的行为。因此,本案中衡大管理处的被诉侵权行为并未侵害河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法润公司享有的“美人榆”品种权”。在“若干规定二”中明确将未经品种权人许可的种植行为评价为生产、繁殖行为进而认定为侵权,无疑为规制商业性大量种植繁殖材料的行为提供了重要路径。
众所周知,植物的繁殖分为有性繁殖和无性繁殖,其中无性繁殖往往具有培育方便且较少变异的特点,能够很好地保留母本的特征特性。以疫情封控期间笔者自行种植小葱为例,只需取小葱不可食用的根部置于清水内,不日即可获得长势喜人的小葱一株。假设该小葱系一种受保护的植物新品种,如果笔者大规模使用此无性繁殖方法通过葱根不断分裂繁殖种植大量小葱并在小区中进行免费赠送,显然会对该小葱植物新品种权的权利人造成严重损害,使其品种小葱市场受到冲击价格受到侵蚀,而笔者种植小葱的事业则会蒸蒸日上。其实,对于无性繁殖的植物而言,种植行为可以分裂和创造出大量新增繁殖材料,其行为本质与“生产、繁殖”无异。特别是一些无性繁殖的观赏类植物,如果行为人在某区域大量种植,即使其不进行售卖,该区域内种植的观赏植物已经可以满足审美需求,充分实现了其商业价值,也明显损害了品种权人销售该观赏植物繁殖材料供他人种植观赏所能获得的商业利益。在《UPOV 1978年文本》第5条中明确规定“Vegetative propagating material shall be deemed to include whole plants. The right of the breeder shall extend to ornamental plants or parts thereof normally marketed for purposes other than propagation when they are used commercially as propagating material in the production of ornamental plants or cut flowers”,其实质上是将保护延伸到了无性繁殖观赏植物及花卉的种植行为。那么,在“若干规定二”已经明确种植行为可以个案认定为生产、繁殖行为后,无疑给认定未经授权种植(某些本身即为繁殖材料的)植物为侵权行为提供了明确依据。值得一提的是,上述举例中,笔者自行繁殖少量小葱供食用的行为属于UPOV条例中的非商业化个人使用,不应认定为侵权。
第三,除了直接侵权行为(生产、繁殖、销售、重复利用)外,几类典型的帮助侵权行为被明确纳入侵权行为范畴,无疑显著加强了对于植物新品种的全链条保护。事实上,“若干规定二”中新囊括的“收购、存储、运输、以繁殖为目的加工处理、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等行为系直接侵权人实施侵权行为的重要助力,上述各个帮助行为是侵权产业链上的重要环节,是直接侵权人成功实施侵权行为、扩大侵权规模、造成侵权损害的得力助手;将该些行为一并纳入侵权行为范畴予以打击显然对加强植物新品种保护有着重要意义。
同时,从诉讼策略的角度来看,由于侵权人实施“生产、繁殖、销售、重复利用”等侵权行为的地点较为固定,因此管辖连接点并无太多选择空间。而加入众多实施帮助侵权行为的行为人后,权利人通过主张直接侵权人与帮助侵权人构成共同侵权的方式,无疑丰富了管辖连接点,从而得以更好地展开一场诉讼。
03
如何定性?
在认定被控侵权物与授权品种繁殖材料是否相同时,应当考察被诉侵权物的特征、特性与授权品种的特征、特性是否相同(或者特征、特性的不同是因非遗传变异所致的)。要作出这种判断,往往需要借助鉴定来查明相关事实。目前司法实践中常见的检测方式包括田间观察检测及基因指纹图谱分子标记检测。其中,分子标记检测包括简单重复序列(SSR),单核苷酸多态性(SNP)和多核苷酸多态性(MNP)等分子标记检测法。两种检测方式各有特点:田间观察检测更多用于品种权的审定,主要为了考察申请品种相较于现有品种是否具有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由于品种植株在田间观察检测中可以充分表达其性状特征,可以直接观察到申请品种与现有品种之间所表达出来性状的异同,因此在田间观察检测中将比较对象确定为被诉侵权物与授权品种,即可直接观察到两者是否表现相同特征特性,从而作出侵权与否的定性。而基因指纹图谱分子标记检测,是基于不同品种遗传物质的碱基排列不同具有高度特异性,从而通过识别遗传物质碱基排列差异来判断是否为同一品种。相较于田间观察检测法,基因指纹图谱分子标记检测具有更客观、更高效的特点,对于在司法程序中及时作出同一性判断具有重要意义。
虽然上述田间观测DUS测试和分子标记DNA检测均能进行同一性判断,但是由于DNA检测所采取的引物(位点)与DUS测试的性状特征之间不具有必然的对应性,因此也存在两种检测结果不同的可能性。为此,“若干规定二”中明确了通过举证责任转移的方式对同一性做出判断,即“当权利人通过基因指纹图谱等分子标记检测方法进行鉴定,待测样品与对照样品的差异位点小于但接近临界值,被诉侵权人主张二者特征特性不相同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也就是说,对于一份确认同一性的DNA检测鉴定意见,被诉侵权人需用一份否认同一性的DUS测试鉴定意见推翻同一性结论,被诉侵权人如不能提交相反证据,法院可以依据DNA检测鉴定意见作出同一性判断。在“金海5号”案中[5],甘肃高院认定:“DNA检测与DUS(田间观察检测)没有位点的直接对应性。对差异位点数在两个以下的,应当综合其他因素进行判定,如可采取扩大检测位点进行加测以及提交审定样品进行测定等。此时的举证责任应由被诉侵权的一方承担。由于植物新品种授权所依据的方式是DUS检测,而不是实验室的DNA指纹鉴定,因此,张掖市富凯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如果提交相反的证据证明通过DUS检测,被诉侵权繁殖材料的特征、特性与授权品种的特征、特性不相同,则可以推翻前述结论。根据已查明的事实,被上诉人富凯公司经释明后仍未能提供相反的证据,亦不具备DUS检测的条件···因此应认定富凯公司的行为构成侵犯植物新品种权。”该案经历二审、发回重审以及重审后的二审,最终在2014年获得生效判决,虽然品种权人一路坎坷,但是该案中确立的通过举证责任转移的方式依据优势证据作出同一性判断的裁判规则,为“若干规定二”23条奠定了基础。同时,司法实践中确有十分耿直的被诉侵权人竭尽全力举证并最终否定DNA分子检测鉴定结论认定同一性的案例。在“先玉335”案中[6],最高院基于被诉侵权人的举证认为“DNA鉴定意见为相同或高度近似时,可直接进行田间成对DUS测试比较,通过田间表型确定身份。当被诉侵权一方主张以田间种植DUS测试确定的特异性结论推翻DNA指纹鉴定意见时,应当由其提交证据予以证明。由于大丰公司提交的涉案DUS测试报告证明,通过田间种植,“大丰30”与“先玉335”相比,具有特异性。根据认定侵害植物新品种权行为,以“被控侵权物的特征特性与授权品种的特征特性相同,或者特征特性不同是因为非遗传变异所导致”的判定规则,“大丰30”与“先玉335”的特征特性并不相同,并不存在“大丰30”侵害“先玉335”植物新品种权的行为”。由此可见,在诉讼双方的对抗中,在鉴定方式以及鉴定结论上的博弈,会是该类案件难以回避的争议焦点。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上述鉴定法判断同一性外,推定与授权品种名称相同的繁殖材料即为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进而转移举证责任,并依此作出同一性判断是在“若干规定二”中首次列明的。该条大大减轻了权利人主张权利时的举证责任。事实上,对于某一品种而言,品种名称是固定的,而且颇具识别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第十八条规定“授予品种权的植物新品种应当具备适当的名称,并与相同或者相近的植物属或者种中已知品种的名称相区别。该名称经注册登记后即为该植物新品种的通用名称”;第四十二条规定“销售授权品种未使用其注册登记的名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林业行政部门依据各自的职权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1000元以下的罚款。”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行政主管部门明确要求相应的品种应当适用唯一的对应的名称,这种规范使用的要求使得不同名称对应的品种之间能够相互区分,也意味着相同品种名称对应的品种应当一致(否则参照假冒注册商标行为处理)。基于上述规则,使用了某一品种名称的繁殖材料应当推定即为该品种繁殖材料,将名称与使用该名称的繁殖材料不同的举证责任转移给被诉侵权人,品种权人的举证责任和难度大大降低。
04
怎样计赔?
侵害植物新品种权案件中,权利人一般可以追索两种费用:临时保护期间使用费和侵权损害赔偿。由于一个品种从申请到获授权需要花费较长时间,而被诉侵权人往往在该品种尚未正式授权前即已经开始实施生产、繁殖该品种的行为,那么针对涉案植物新品种申请初步审查公告后到被授权之间的这段期间,如有未经许可擅自生产、繁殖涉案品种的繁殖材料的,权利人可以主张该品种的临时保护期使用费。当然,该临时保护期使用费需要在涉案品种被授权后再行主张,否则品种权尚未形成也即不存在该临时保护期使用费。类似的,在专利案件中,权利人有权要求发明专利申请公布日至授权公告日期间实施该发明的单位或者个人支付适当费用。在植物新品种案件中,临时保护期的设置无疑也扩展了对于植物新品种的保护期限,使得已申请但尚未授权期间的权益也能够得以充分保障。追索临时保护期使用费纠纷的案由为临时保护期品种权许可费纠纷。对于未经许可擅自生产、繁殖品种繁殖材料的行为横跨该品种授权时间点的,对授权前的行为应以“临时保护期品种权许可费纠纷”主张,对之后的行为以“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主张,法院可以合并审理,但是对于临时保护期品种权许可费和侵权损害赔偿应当分别计算。在“华美105辣椒”案中[7],法院认定“本案中,华美公司并未许可他人实施“华美105”植物新品种,故无许可使用费可供参考。本院综合考虑如下因素:“华美105”作为辣椒属新品种,属于常见蔬菜品种;从在案证据尤其是夏中福“一年出10000多包,都用好几年了”的自述,以及夏中福从山东将侵权种子销售到甘肃省酒泉市来看,该品种经营规模较大、具有较高市场价值;华美公司以260元/包的价格销售“华美105”种子,而夏中福本案的销售单价为150元,两者差价110元,可作为确定临时保护期使用费的依据之一;“华美105”的初步审查合格公告日为2017年3月1日,授权日为2018年7月20日。结合上述因素分析,本院酌情确定本案临时保护期使用费为45万元·····并综合考虑其侵权主观恶意、侵权手段、销售侵权种子的价格、侵权行为的持续时间、地域范围等因素,按照侵权获利的计算方式确定赔偿数额。如前所述,本案中针对“华美105”应支付的2018年7月20日前的临时保护期使用费已另行计算,侵权损害赔偿则自此之后予以起算。夏中福以315000元的价格向王福销售种子2100包,而其微信自述一年出10000多包,故按其陈述认定销售总额为10000包,其侵权销售额可计为315000×(10000/2100)即150万元,在此基础上本院合理考虑利润率,确定夏中福的侵权获利为45万元”。该案例清楚体现了临时保护期许可费和损害赔偿分段主张、分别计赔的裁判规则。 适用惩罚性赔偿计算赔偿是加大植物新品种司法保护力度的重要措施。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知识产权民事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的基础上,“若干规定二”结合植物新品种案件侵权行为的特点,补充了新的认定“情节严重”的因素,包括“以无标识、标签的包装销售授权品种;未取得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生产经营种子”等,而且就某些具体的“情节严重”行为类型,规定了需要在基数基础上以2倍以上确定惩罚性赔偿数额。在“金粳水稻”案中[8],法院认定“对于原告提出适用惩罚性赔偿的主张,法院认为,被告未经许可采用白皮或其他不规范的包装销售种子,其中无任何有关种子信息的标注,侵权方式隐蔽,主观故意明显,侵权情节严重,不仅侵害了原告获得的植物新品种权之独占实施权,还严重损害了种子生产销售秩序,存在可能严重损害品种购买者、种植者的利益以及造成实际损害,故对原告的该赔偿主张予以支持,即按照上述赔偿计算方法所确定赔偿数额的三倍作为最终的赔偿数额”。无独有偶,在“金粳818”案件中[9],法院认定“综合考虑(被告)亲耕田公司的侵权恶意、手段、规模和范围等,尤其是亲耕田公司未取得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以无标识、标签的包装销售授权品种,亲耕田公司属侵权情节严重·····对于亲耕田公司在依法适用惩罚性赔偿时可以按照计算基数的二倍以上确定惩罚性赔偿数额”。可见,一些具有“植物新品种特色”的情节严重情形正在司法实践中被一个个鲜活的案例不断唤醒;而事实上,这些情形之所以被认定为“情节严重”,也恰时因为其在种子生产和流通环节中可能对种质资源的购买者和种植者造成的严重危害。
05
停或不停?
在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中,能否以及何时能够让被控侵权人尽快停止侵权行为是品种权人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在大多数案件中,如果法院经审理认定被诉侵权材料系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一般会支持品种权人要求对侵权物作消灭活性等使其不能再被用作繁殖材料的处理。如此,即可达到禁止被诉侵权人继续以侵权物继续实施生产、繁殖、销售等行为。
为了防止此类案件审理周期过长导致品种权人的利益受到持续侵害以及损失的进一步扩大,与其他知识产权类似,侵害植物新品种案件中同样适用现行判决以及临时禁令。一旦出现案件定性清楚但计赔繁复的情形,品种权人即可申请法院先行判决,就侵权部分现行作出判决,责令被诉侵权人立即停止其侵权行为。同时,根据个案情形,品种权人也可以申请临时禁令要求对于被诉侵权的繁殖材料采取消灭活性等措施防止被诉侵权物扩散和继续繁殖。通过先行判决适用,可以更短的时间定纷止争;通过临时禁令的颁发,亦可弥补一审判决尚未生效时缺乏执行力的问题,防止被诉侵权人通过二审程序拖延诉讼进程导致侵权规模进一步扩大。
但是,法院并非在所有侵权案件中都会判令停止侵权,当销毁侵权物会造成严重不利后果或者有损公共利益甚至影响粮食安全时,可以采取其他方式弥补品种权人的损失。比如,被诉侵权物是大面积多年生长的侵犯品种权的稻米,责判令销毁该些稻米植株不但损害了广大种植农民的利益,同时也会造成严重的粮食浪费,此时就不宜简单地判决停止侵权、销毁侵权物。在“9优418水稻”案中[10],法院认为“天隆公司与徐农公司不能达成妥协,致使9优418品种不能继续生产,不能认为仅关涉双方的利益,实际上已经损害了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实施,有损公共利益,且不符合当初辽宁稻作所与徐州农科所合作育种的根本目的,也不符合促进植物新品种转化实施的根本要求。从表面上看,双方当事人的行为系维护各自的知识产权,但实际结果是损害知识产权的运用和科技成果的转化。鉴于该两案已关涉国家粮食生产安全等公共利益,影响9优418这一优良品种的推广,双方当事人在行使涉案植物新品种独占实施许可权时均应当受到限制,即在生产9优418水稻品种时,均应当允许对方使用已方的亲本繁殖材料,这一结果显然有利于辽宁稻作所与徐州农科所合作双方及本案双方当事人的共同利益,也有利于广大种植农户的利益,故一审判令该两案双方当事人相互停止侵权并赔偿对方损失不当,应予纠正”。类似的,在“郑单958”案中,法院考虑到被告德农公司已经为生产“郑单958”杂交种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若禁止德农公司使用母本“郑58”自交种生产“郑单958”玉米杂交种,将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可采用支付一定赔偿的方式弥补金博士公司的损失,故判决德农公司赔偿损失及合理开支4952万元。事实上,法院虽然没有判令停止侵权,但是将“郑单958”品种剩余品种权期限折算成许可费,责令被告一次性支付该笔许可费,从而既避免了被告遭受巨大经济损失,也对品种权人给予了充分救济。
注释
[1](2019)最高法知民终 14 号
[2](2021)最高法知民终816号
[3](2014)鲁民再字第13号
[4](2018)最高法民再247号
[5](2013)甘民三终字第63号
[6](2015)民申字第2633号
[7](2021)最高法知民终1469号
[8](2020)苏01民初226号
[9](2021)最高法知民终816号
[10](2011)苏知民终字第0194号

扫码添加知产力小管家,注明姓名+单位+植物新品种
即可直接获取本文9件判决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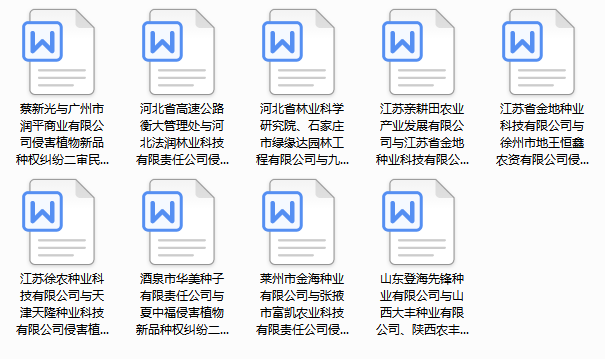
(图片来源 | 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