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文聪:论著作权法中的“表演”与“表演者”(三)——“表演行为”的周延表述
知产力(微信ID:zhichanli)
知产力是一家致力于“为创新聚合知识产权解决方案”的原创型新媒体平台。关注科技领域创新及相关知识产权问题,请订阅本微信公众号(zhichanli)、官方微博:知产力,亦可登录www.zhichanli.com查阅更多精彩内容。
作 者 | 熊文聪 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高级访问学者
(本文系知产力获得授权的稿件,转载须征得作者本人同意,并在显要位置注明文章来源。)
[书接上文]
摘要
法律概念服务于定纷止争、治理社会的实践目的,而非对客观事物的单纯描述。“表演者”概念的核心在于“表演”,但现行著作权法却未能清晰地界定这两个概念,导致司法裁判的不一致和不确定。基于既定的价值考量和逻辑分析,我们可以从“表演行为”、“表演对象”、“表演主体”三个层面递进式地推敲和框定“表演者”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从而回应和解答具体案件中的诸多难题与争辩,并为今后《著作权法》的修改完善提供智识性的帮助和指引。
三、“表演主体”的逻辑构成
根据《著作权法》第37条的规定,表演者包括演员和演出单位。也就是说,表演者既可能是自然人,也可能是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相关解释是:“我国《著作权法》承认法人作者地位的合法性,自然在承认表演者的主体包括自然人及其他组织的问题不存在障碍——表演者包括自然人的表演者及演出单位,即剧团、歌舞团等表演法人及其他组织。”[31]这种立法例将实际表演者与表演者权(特别是其中的财产权)权利主体混为一谈,与《罗马公约》、《表演和录音制品公约》和《北京条约》对表演者的界定均不相符合。有研究者指出:“表演作品,需要表演者对作品进行理解和阐释,需要通过表演活动将表演者对作品的理解外化出来,只能由自然人进行,法人不可能具有这样的的判断、理解和表达能力。”[32]在“广东唱金影音有限公司与中国文联音像出版社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戏剧类作品演出的筹备、组织、排练等均由剧院或剧团等演出单位主持,演出所需投入亦由演出单位承担,演出体现的是演出单位的意志,故对于整台戏剧的演出,演出单位是著作权法意义上的表演者,有权许可他人从现场直播或录音录像、复制发行录音录像制品等,在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演员个人不享有上述权利。” [33]这显然是类推适用了《著作权法》第11条第3款“法人作品”的规则。但需要注意的是,《著作权法》对于作者人格权和著作财产权的归属设定了多种不同的模式,包括一般自然人作品、法人作品、职务作品、委托创作作品、视听作品等等,最高人民法院并没有就其选择“法人作品”这一模式给出充分理由。同样地,在“陈涛、胡海泉诉上海联家超市有限公司案”中,审理该案的人民法院认为,涉讼歌曲并不体现演出单位的意志,而是“由两原告演唱的,该演唱主要依靠两原告自身的形象、动作、声音等完成,体现的是两原告自己的表演意志,故两原告是其表演所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的主体,涉讼22首歌曲的表演者权应属两原告。而被告所称的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是该场演唱会的组织者而非表演者。” [34]可见,在表演者身份认定这个重要问题上,不同人民法院虽然都采用所谓的“意志说”标准,却可能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这无疑放大了司法裁判的不确定性和随意性,降低了法律的稳定性和权威性。基于此,《送审稿》(2014)第33条将演出单位排除出表演者范围,明确指出:“本法所称的表演者,是指以朗诵、演唱、演奏以及其他方式表演文学艺术作品或者民间文学艺术表达的自然人。”该规定与国际条约保持一致,值得肯定。
司法实践中,关于表演者界定的另一个热点问题是:视听作品中的演员是不是表演者,其是否可以就视听作品中的表演主张表演者权?根据《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5条第(6)项对表演者的界定,但凡演员都属于表演者,故依照体系解释,视听作品中的演员享有《著作权法》第38条规定的表演者人格权和表演者财产权。然而,《著作权法》第15条第1款又规定:“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的著作权由制片者享有,但编剧、导演、摄影、作词、作曲等作者享有署名权,并有权按照与制片者签订的合同获得报酬。”也就是说,视听作品的编剧、导演、摄影、作词、作曲等作者除了享有署名权和获取报酬的债权,并不享有此视听作品的著作财产权和其他作者人格权。这就出现了一个逻辑上的疑问,即同样是视听作品的创作参与者,甚至其对创作该视听作品的贡献更大,为什么编剧、导演、摄影、作词、作曲等作者的法定权利要少于(或弱于)演员呢?此处的“等作者”是否包括“演员”在内呢?
在“高健诉梅赛德斯-奔驰(中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案”中,审理该案的人民法院指出:“虽然涉案广告片中包含了高健作为演员的表演,但其参与涉案广告片的表演系带有劳务性质的履约行为,其为涉案广告片拍摄所进行的表演属于涉案广告片的一部分内容,并且与声音、场景画面相结合形成了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即涉案广告片。在涉案广告片的整体著作权依法归属于制片者的情况下,高健作为该作品中的表演者,其所从事表演部分的权利已经被吸收,其在享有表明表演者身份及保护其形象不受歪曲等人身性权利的同时,仅享有依据合同获得报酬的权利,而不再享有其他经济权利,无权对其在广告片中的表演单独主张表演者权。……表演者权在著作权法意义上是一种邻接权,是表演者作为作品的传播者因表演他人作品所享有的一项权利。在著作权与邻接权的保护上,著作权法保护的重心是著作权,对邻接权的保护不能超越著作权。根据‘举重以明轻’的法律解释方法,既然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的相关作者都不能对该作品行使复制权、发行权等专有权,表演者当然也不应有权行使上述权利”。[35]可见,该案采取“举重以明轻”这一“当然解释”方法,认定视听作品中的演员因为有《著作权法》第15条第1款之规定,故不得再主张《著作权法》第38条规定的表演者财产权。虽然该案的结论可以接受,但其路径却值得商榷。所谓“当然解释”,是指“法文虽未规定,惟依规范目的衡量,或逻辑上之推论,其事实较之法律所规定者,更有适用之理由,而径行适用该法律规定而言”。[36]也就是说,只有在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况下,才可能运用当然解释,从而适用已规定之事项。既然《著作权法》第38条已经规定了表演者享有“许可他人复制、发行录有其表演的录音录像制品,并获得报酬”这一财产权,且法院认为广告片中的演员也是表演者,就应该直接适用第38条,而不是采用所谓的“举重以明轻”及“权利被吸收”而转由适用第15条,将第38条的明文规定置之不顾。实际上,法院的判决结论是合理恰当的,只是用错了解释方法。笔者认为,应首先将《著作权法》第38条的“表演者”作限缩解释,即只有其表演在整个演出(包括视听作品)中起“举足轻重、不可替代”作用的人,才能称之为“表演者”,享有表演者权。这一限定也回应了当初主张通过立法保护表演者权的多为音乐和戏剧表演者的历史。[37]相反,视听作品中的非主要演员虽然参与了创作,但是没有起到“举足轻重、不可替代”之核心作用,如本案中的平面模特高健在这个广告中仅仅起到点缀作用和附属效果,故不能将其界定为著作权法中的表演者,不能享有表演者权,而只能“类推适用”《著作权法》第15条或将第15条作扩大解释,因为视听作品中的演员与编剧、导演、摄影等作者一样,通过其姿态动作、表情声音的个性化表达参与了视听作品的创作,只有如此解释,逻辑上才较为圆满。
当然,要区分视听作品中的“主要演员”和“非主要演员”,并分别适用不同的法律规则,进而得出截然不同的法律结果,确实会给法官制造难题,这需要最高人民法院在总结裁判经验的基础上给出一定的指引和标准。也许正是意识到《著作权法》第15条一概否定视听作品中的演员(即使是“非主要演员”)享有著作财产权之做法有失公允或者难以区分,《送审稿》(2014)第37条才试图将其改为:“制片者聘用表演者制作视听作品,应当签订书面合同并支付报酬。视听作品中的表演者根据第34条第(5)项和第(6)项规定的财产权及利益分享由制片者和主要表演者约定。如无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前述权利由制片者享有,但主要表演者享有署名权和分享收益的权利。”该项规定以及《送审稿》(2014)第19条第3款与现有规定相比,增加了导演、编剧、专门为视听作品创作的音乐作品的作者等视听作品的作者、主要表演者与制片者进行谈判的筹码和“二次获酬”的机会。实际上,著作权法打破市场惯例、创设特定权利,旨在倾向性地保护弱者,如当初法国通过确立追续权来保护画家的权益。[38]但在现代传媒商业环境下,作为主要表演者的一些明星、大腕是否还是弱者?这一立法模式是否会徒然增加电影制作及交易成本,与市场活动的正常运转相抵牾?是否符合当下的实践需求?尚值得广泛调研与深入思考。
结 语
概念是思维的结晶,也是推理与判断的起点,正所谓“回答首先取决于定义。”[39]然而我们需要谨记:法律中的概念并不能与生活中的相同语词直接划等号。法律服务于“有效治理社会”这一实践目的,是对人们行为的一种约束和指引,强调“当为”,故法律概念中总是包含价值判断,而非对客观事实的单纯描述。在界定著作权法中的“表演者”及“表演”概念时,应从表演行为、表演对象和表演主体三个层面着眼,并首先考虑表演者权保护了哪一主体的利益,同时又给哪一主体设定了义务,或限制了哪一主体的行为自由,如何在不同主体间进行平衡,从而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基于此,我们需要考量是否应当将具有一定艺术表现力和独创性的文体活动界定为表演活动或者作品,从而激励创作和投资;视听作品中演员的二次获酬权是否与中国相关行业的惯例相悖,从而有可能增加交易的成本,阻碍创意产业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概念界定也必须满足逻辑上的周延。我国采邻接权与著作权分立体系,表演必须与原创有所区别,故表演只能是自然人通过姿态动作、声音表情或乐器道具等,对“既有作品”进行演绎表达,以供他人欣赏的行为。“即兴表演”乃日常生活用语,并不属于著作权法中的“表演”及邻接权范畴,但完全可以作为口述作品、舞蹈作品、音乐作品、戏剧作品或曲艺作品等受著作权保护,从而保证法律体系的自洽性。同样地,由于表演只能由自然人实施,故“机械表演权”应表述为“机械再现权”或纳入“播放权”。表达展示民间文学艺术如果体现了创作者的取舍、安排、设计和组合,可以就其独创性部分主张著作权保护,但无法将其界定为“表演”(因没有“既有作品”)。具有观赏性的动物表演可以获得著作权或邻接权保护,理由不是把动物当做“自然人”,而是该创作者或表演者本身就是自然人——训练该动物的驯养员。同理,法人等组织体由于客观上不能进行表演,故无法成为表演者,但完全可以成为表演者权(财产权部分)的权利主体。由此观之,法律上的概念往往是价值判断和逻辑推演相结合的产物。
注 释:
[31] 胡康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53页。
[32] 陈锦川:《对现行<著作权法>几项具体制度的修改建议》,《中国新闻出版报》,2011年8月11日版。
[33]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8)民三终字第5号。
[34] 参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6)沪一中民五(知)初第190号。
[35]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三中民终字第03453号。
[36] 杨仁寿:《法学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58页。
[37] 参见原晓爽:《表演者权利研究》,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41-45页。
[38] 参见李琛:《求生计米勒忍埋半世名,感悲情法律新设追续权》,《科技与法律》2004年第2期。
[39] [美]萨托利:《民主新论》,冯克利、阎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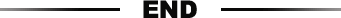
本文原载于:《法商研究》2016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