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 | 刘文杰:大数据时代以前并非不存在大数据
知产力(微信ID:zhichanli)
知产力是一家致力于“为创新聚合知识产权解决方案”的原创型新媒体平台。关注科技领域创新及相关知识产权问题,请订阅本微信公众号(zhichanli)、官方微博:知产力,亦可登录www.zhichanli.com查阅更多精彩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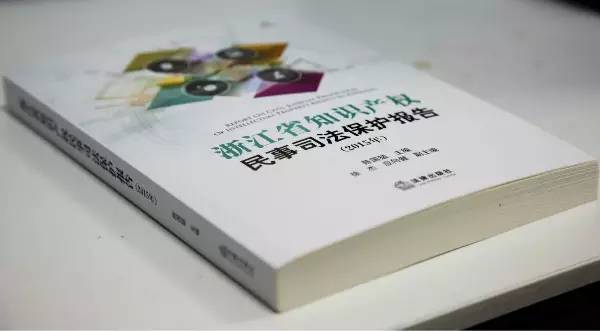
主 编 陈国猛
副 主 编 徐 杰 应向健
——评《浙江省知识产权民事司法保护报告( 2015年)》
作 者 | 刘文杰 中国传媒大学文法学部网络法与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本文系知产力获得独家首发授权的稿件,转载须征得作者本人同意,并在显要位置注明文章来源。)
大数据时代以前并非不存在大数据。所谓大数据时代,其特征首先在于人们对于数据的再认识,认识到数据挖掘能够产生前所未闻的巨大价值。大数据时代实际上就是人们自觉运用技术对各类数据加以系统性挖掘和利用的时代。因此,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是一个越来越多的人发生观念革新的过程。一开始是星星之火,积数年而成燎原之势。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浙江省知识产权民事司法保护报告( 2015年)》就是这种大数据观指导之下的产物。
众所周知,相对于企业和个人,公共职能部门所掌握的数据可谓是真正的大数据。如何让这些数据公开在阳光之下,为民所用,不但是一个技术问题,在当前体制之下,更取决于任事者的眼界与决心。出版一部知识产权审判数据挖掘成果,其意义不待多言。而要将相关信息形成完整周延的数据系统,其难度可想而知!
当前,对于知识产权民事司法数据的处理大多停留在数据统计阶段,尚没有达到大数据整合与挖掘的层次。这一情况的存在当然有其原因:原始数据散见于各类司法裁判文书,相当一部分信息甚至在裁判文书中也没有体现,而一线法官坐堂听案,无暇他顾,况且数据分析亦非其职责所在。浙江省高院知识产权庭知难而进,集全省同仁之力,成为这一领域的吃螃蟹者,一时领风气之先。阅读本书,亦可想见法官们在收集和整理数据上所付出的巨大辛劳。
本书旨在“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从直觉与经验主导转向理性思维决策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故一方面在数据上全方位涵盖浙江省内知识产权民事审判的整体规模和结构、涉诉主体、权利类型、侵权行为类型、证据与程序、损害赔偿及结案等关键节点信息,全景式展示一省知识产权民事司法审判的全貌,另一方面,则超越对数据的简单收集与罗列,通过对大量信息的梳理、整合、分析,将其中蕴含的区域性司法保护规律完整地加以呈现。
书中既有对浙江全省知识产权民事司法保护总体情况的归纳总结,又有对省内各地市的知识产权民事司法保护情况的耙梳厘清。具体到四类知识产权案件信息的类型化梳理,包括每一类型案件内部的裁判、调解、和解等结案方式的信息处理,编著者的工作细致到一一列表、制图,力求以可视化形式向读者呈现的程度。当然,书中也不缺乏在摸底、归纳和整理之后就相关民事纠纷案件发生规律及其成因的深入分析。
就此而言,本书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使社会公众更全面细致了解一省之内的司法审判现实,还有利于律师、当事人提高对司法审判的预期,亦可为决策者、研究者引为重要参考。
而在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件中,占有极高比例的行为类型分别是擅自使用他人的企业名称或姓名而引起误认、与知名商品相混淆以及假冒他人的注册商标,说明反不正当竞争的主要侵权行为类型仍然是搭便车行为,调整此类行为的规则仍然是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核心条款。进入互联网时代以后,网络上同样出现大量不正当竞争行为,这些行为有些可能属于花样翻新,但更多的仍然可以归入传统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类型。
大数据分析不但能够揭示法律实施状况,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经济生活的某些特点。例如,本报告显示,2015年全年浙江法院受理案件中商标权专利权的案件占比不足三成,而著作权的比例偏大,这和人们的经验印象一致,但在著作权争议案件中,KTV著作权侵权案件又占到了全部著作权案件的六成以上,则反映出本省KTV经营模式的某些特征。再如,许多案件的被告是便利店、小超市,这些所谓“草根案件”和“牛皮癣案件”同样反映出经济行为链条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一个地区内知识产权民事纠纷案件的体量如何,通常与该地区经济发展的规模与水平相关,但也可能与本地区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水平相关。随着经济的增长,当事人的维权意愿往往也随之上升,如果同时伴随司法保护水平的上升,当事人趋向保护周延的地区开展维权,也就成了自然的事情。换言之,法律纠纷的体量较大并不意味着本地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水平的低下,情况也可能恰恰相反,就此,本书的数据和分析可作参考。
法谚有云,无权利则无救济,这一格言落实到司法审判中,则为无证据者则无救济。鉴于举证对于司法审判的关键意义,本书专门梳理了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的举证情况,给人们提供了一个直观审视当下证据机制的视角。
例如,数据显示,在民事案件的证据采集方式中,公证取证占有极高的比例,自行取证位居其次,法院取证的比例较低,呼声甚高的第三方电子证据保全在各类案件中的比例却都相当之低。出现此种现象的根源何在?
公证证据在司法裁判中一枝独秀,固然与这种证据较强的公信力有关,但也说明了法院对公证可能存在过度依赖和对当事人举证的信任不足。这种不信任又会抑制当事人的举证热情,反过来加重对公证的依赖,造成恶性循环。尤其是在电子证据形式屡见不鲜的今天,越来越多的案件证据将不可避免地表现为易修改、难追溯的电子数据形式,在这种情况下,一味地将责任推给并不具备太多证据甄别能力的公证处,恐非妥当。
在本书中,编著者既对公证取证方式在知识产权民事案件取证方式中一家独大的局面给出了较为合理的解释,也坦率地承认,公证并非万能,也有自身的不足之处,随着电子数据的日益普遍和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公证证据也面临着全新的挑战。对此清醒认识可资赞同。在其他问题的揭示上,例如对于举证妨碍问题和法定赔偿适用问题,本书也表现出了令人称道的坦率。
举证妨碍是另一个近年来讨论较多的话题。本书的统计显示,在2015年浙江省全省知识产权民事案件中,使用举证妨碍的案件只在商标权纠纷案件中存有一件。各方面认为应当积极采纳的制度在实践中却处于休眠状态,不啻说明,制度从口号落实到实际的距离比人们想象的要长得多。本书没有回避这一问题,而是指出,举证妨碍制度没有落地,在一定程度上与法院的审查标准过严有关,对策是适当降低对于举证妨碍规则的审查门槛,对于举证过程中严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要加大损害赔偿义务力度,坚决予以制裁。
损害赔偿数据分析是本书的另一个亮点所在。统计结果显示,正如人们所推测的,法定赔偿在知识产权侵权赔偿中所占比例极高,2015年,在浙江省知识产权审判民事案件中,专利权、著作权类案件适用法定赔偿的比例均超过九成,商标类案件适用法定赔偿的比例也超过了八成。这意味着,在绝大多数案件中,法官不是按照证明损失数额的证据,而是根据自己的心证来决定赔偿数额的。和有关公证的讨论一样,出现这一情况,既有当事人一方的原因,也有法院如何运用举证规则的问题。本书对此进行了揭示,并批评了部分裁判文书关于法定赔偿的说理存在讲套话而影响裁判文书公信力的现象。
大数据时代,人们有了对数据价值的认同,“但是,当数据处于碎片化状态时,数据资源的价值仍然难以充分发挥。”职是之故,对碎片化状态的知识产权民事司法数据加以系统的挖掘和利用,让原本杂乱无章的数据呈现出新的面目,遂成为本书使命所在。作为破冰者,这本由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联合知产力、知产宝出品的报告很好地完成了这一使命。
当前,社会各界对司法公开一片叫好之声,但也常存忧虑,担心其令行之不远,中道而废。其实,只有更加坚决地推行司法公开,给公众以充分的信息,才能提高司法公信力,保护法官自己。所谓“令初下,群臣进谏,门庭若市”并不可怕,只要坚持公开,则“数月之后,时时而间进,期年之后,虽欲言,无可进者”。从这个意义上讲,本书也是对最高人民法院司法公开路线的有力贯彻,值得为其喝采。




















